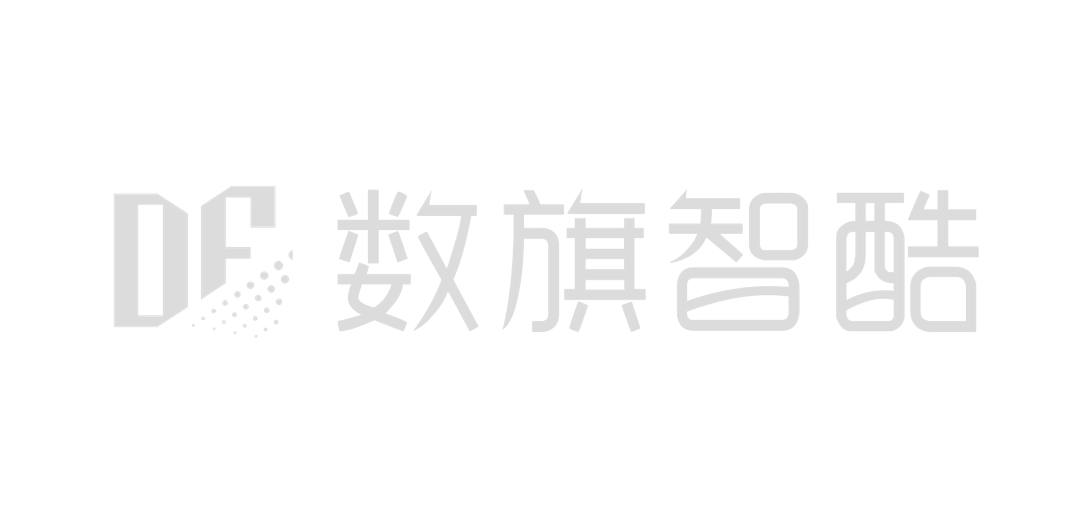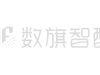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本文为《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Urban China》的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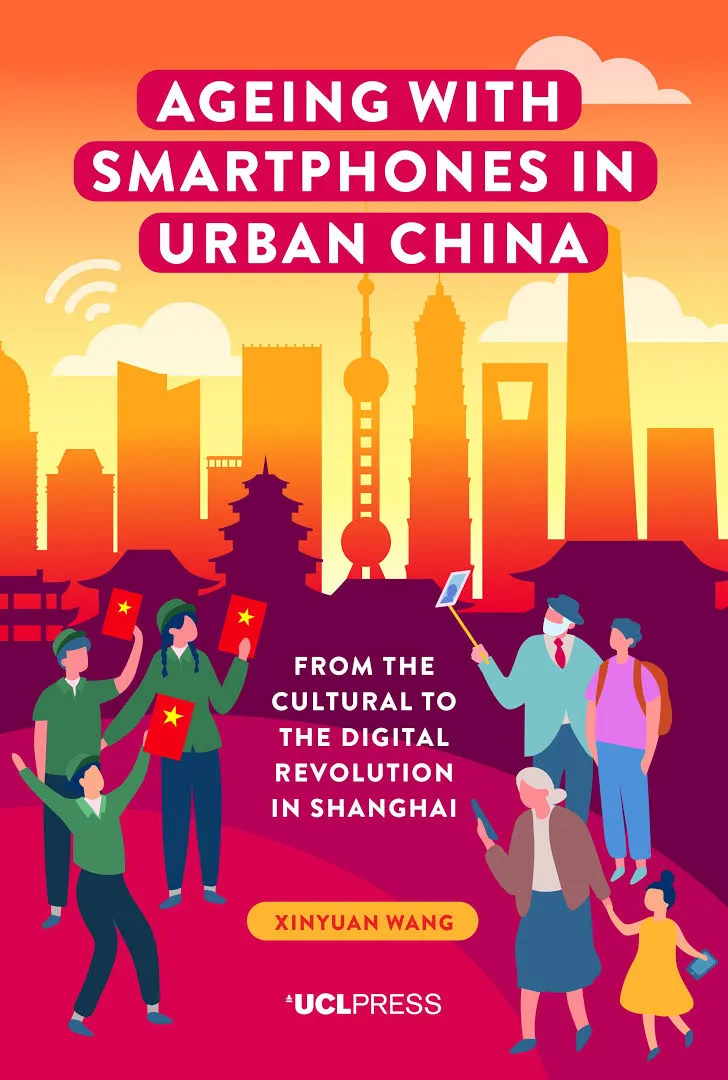
在一个老龄化曲线异常陡峭的社会谈论智能手机的应用,通常让人想起的都是与“信息无障碍”、“数字包容”、“数字鸿沟”等相关的技术叙事,而忽略了其在地性、历史感、政治根源以及文化记忆在其中的作用与角色。
伦敦大学数字人类学研究学者王心远所著的《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Urban China》一书,为我们重新思考技术、历史、社会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研究框架:通过在上海对1945年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且完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的智能手机应用行为的田野调查,将今天正在发生的数字革命与六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通过个体经验、集体记忆与行为、遗产等进行连接,观察这一代人如何通过智能手机来参与和拥抱数字革命,从而说明六十多年的那场运动如何影响今天的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方式,以及他们在数字交往过程中秉持着何种心理,以及期望达到何种目的。
当然,本书并不仅限于老龄化与智能手机的讨论,作者还试图从这一代人的精神、行为、话语、经验与记忆中,延展到中国社会的“关系”、“面子”、个人主义、儒家思想等思考。
从曾经的“耻辱可恨的半殖民地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受欢迎的残余”,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与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全球化城市,被冠以“魔都”、“远东巴黎”等称号的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与数字革命的共同洗礼下,正在绽放“既古老,又年轻”的气息。但上海对于中国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1920年,《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中文,几乎与此同一时间,《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的里弄中秘密流传开来。革命的种子就此播撒。1921年,在上海的前法租界内一处典型的“石库门”式里弄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来因为被特务破坏转而到嘉兴游船继续召开。之后才有今天的“红船精神”。
1965年,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在上海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995年上海电视台拍摄的作家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讲述了一群返城知青的子女从遥远的西双版纳到上海寻亲的故事,其背景就是文革期间的知青下乡。
根据上海市卫健委2023年10月23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12月31日为止,全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553.66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6.8%。上海已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在上海的城市历史中,包含了对前沿新思潮的选择(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其实是一种“小众思想”;《毛泽东传》/史华慈)、拥抱革命的勇气、被时代裹挟的激进以及社会剧变中的惆怅与迷惘。现在,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产业与“老龄化”再次成为全球城市转型发展中的重要话题。
当年在红色海洋里热火朝天坚持革命理想的年轻人,如今正在以新的“革命激情”来参与和拥抱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数字革命,他们如何回忆和叙述上一次革命?以及如何处理自己进入老年后与“新的革命”的关系?这或许是作者王心远希望在《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Urban China》告诉我们的。
从文化大革命到数字革命:“券”、“螺丝钉”与“忠字舞”的当代回响
告别一个时代的方式有很多种,无法斩断的是在代际传承中的文化记忆与集体经验。如果要说从文化大革命到数字革命,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与生活经验无法否定的是什么?那应该是作为民族国家与国家权力在个人生活空间中的“划痕”,它们通过“单位”、“户口”、“介绍信”、“工分”等方式,最终形成了一个国家的记忆。
“券”,作为一种横跨国家改革进程的金融性凭证,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产生的是不同的心理反射。对于文革一代而言,计划经济时代的“券”是一种稀缺的代名词,是一种与生存有关的凭证,粮食、肉、糖等都需要凭券购买,这种“券”与支付及物品价值无关,它代表一种身份与系统对生存需求的认可。而数字经济时代的“券”则代表一种物质上的丰沛,是一种自由市场的营销手段,代表一种与支付有关的优惠机制。所以,当一位文革一代的老人用“券”抵消了快递费用从而可以免费上门获得购买的商品时,他获得的是一种额外的满足感,但这同时也会让他们回忆起那个困难年代由“券”引发的锱铢必较的窘迫感。从计划经济到数字经济,“券”已从一种对人格的“惩罚”变成了一种对生活热情的“奖励”。
我们已然很难感受到“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对文革一代人具有多么致命的吸引力,而“螺丝钉”似乎依然保持了其原有的本意,只是它所依附的主体发生了改变。以前是“革命是机器,我是螺丝钉”,现在是“公司是机器,我是螺丝钉”。这种“人与机器”的关系也正在被数字技术进一步刷新:平台是机器,我们都是螺丝钉。这里的“螺丝钉”将不再包含任何雇佣、隶属关系,它泛化到每一个人的数字化生存状态。
但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绵延几十年至今,“螺丝钉”主义背后的“个体”、“自我”和“人格”正在觉醒,“大厂”的高薪也开始无法抑制住对“996”、“007”以及“福报”的反抗,“一人公司”、“超级个体”、“自媒体”等都成为“螺丝钉”们抵制去个体化进程的一种表现。只是作为文革一代的老人,他们漂浮在一个弥漫“去个体化”思潮的数字革命海洋中,却依然坚持“螺丝钉”的某种纯洁性。
当年轻人试图“断网”、“社交斋戒”、关闭朋友圈的时候,老一代人继续沉溺于享受作为一颗“螺丝钉”的价值,每天转发中医、孝道与做饭短视频忙得不亦乐乎。
“忠字舞”则更具时代特色,并锚定在那个特殊的“红色偶像”年代。与一般历史学者或政治学者的看法不同,作者不认为老人喜欢“红卫兵”摄影与“忠字舞”是对那个荒谬时代的恋恋不舍或“招魂”,作者还试图对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祛魅”。她认为,这一代老人之所以怀念那个时代,并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困顿、悲伤、疼痛与苦闷,以及破罐子破摔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而是怀念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在尚不具备是非分辨能力的青春期中留下的精神遗产——那种热烈而恣肆的东西今天被称之为“正能量”。
他们将智能手机所激活和唤醒的那种热情重新投入到当下的生活场景中,并以一种学习的姿态不断适应这个数字时代的变化。比如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研究如何进行朋友圈信息分组,比如他们会研究微信群如何发送和回复表情包以及“数字交往伦理”,比如他们会因为避免尴尬而“艺术地”解散微信群。所有的一切都暗示着他们对正在发生的数字革命时代的向往、投入与沉醉。这不是仅仅用“老人爱学习”可以解释得了的。
如果说“忠字舞”是源自一种有形的效忠对象与崇拜对象的控制,那么基于智能手机的应用行为则可能就是流量和算法导致的无形控制。只是后一种控制包含了前一种控制的精神侵蚀。
今天的“忠字舞”消失了么?并没有。它以一种文化变体与消费主义媾和,开始吸附或宿居于火锅店、理发店、洗浴中心、传销公司等各种商业体内。他们以“忠诚”作为企业文化建设核心,尽管他们非常年轻,尽管他们极为现代地运用各种技术和设备,但他们似乎认为上个时代的革命叙事比任何现代企业管理理念都更为高效。或许只有在一套具有历史记忆且相互熟悉的叙事中才能构建一种看似稳固的群体安全感。
从“券”、“螺丝钉”与“忠字舞”,从文化大革命到数字革命不只有这些我们所常见的“当代回响”。如果在公园、景区仔细观察,你一定会发现,文革一代的老人,他们用智能手机自拍的姿势与当年手捧“红宝书”的姿势,极为相似,他们都希望通过姿势构建的忠诚表达以获得来自远方的肯定。有所不同的是,“红宝书”让他们看见的是一个模糊的“精神自我”,而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可以让他们看见一个被数字增强的现实自我。相同的是,这个“自我”分别被意识形态滤镜或数字滤镜进行了修饰与“磨皮”。
数字革命的文化根脉:“关系”、“面子”、“组织”以及“革命友谊”
将个人生活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形式复制,这或许是文革一代老人找寻智能手机应用的意义感的方式。将“关系”、“面子”、“组织”以及“革命友谊”在智能手机的社交应用上进行移植,从而实现自我在数字空间中的重生,并找到自己作为“退休人员”的价值所在,这是数字革命赋予他们的意义。
“关系”这个词的涵义丰富到连英文都只敢翻译为“guanxi”。如果纳入到中国的社会交往中来理解,关系(guanxi)应该是关于情感、利益、友谊、交换、虚荣的总和,是一种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与价值评估系统。“关系”与“做人”密切相关。
作者提到一位老人为了孙子上小学择校的事,通过曲折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曾经疏远的远亲,在加为微信好友之后,他们通过朋友圈展示、点赞以及晒情绪等方式,潜移默化地不断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密度。直到最后,通过自我的情绪扩展而“逼迫”对方主动引导出自己的真实需求——即孙子上小学需要择校。而这位远亲的一位后辈刚好在目标小学担任副校长。以“非正式沟通”达到正式沟通的目的,恰恰是将“关系”和“做人”发挥到极致的操作方式,它包含了对人情的洞察、时机的把握以及分寸感的拿捏。而这对于文革一代而言,革命浪潮的跌宕起伏已让他们将塑造“关系”的技能修炼得炉火纯青。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的作者翟学伟指出,“因为权力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任意性,因此操作权术本身就合情合理,进而用人情攀上权贵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获得权力的转让,实现权力的再生产,我称其为‘日常权威’”。通过微信的互动提升人情的热度,实现关系的升温,进而将作为“副校长”的权力在自己的孙辈身上实现再生产。
当然在人情和关系构筑的权力再生产流程中,“意外”也可能随时发生,这需要双方共同维持一个绝对的“沉默平衡”——即我知道你和我保持良好关系的目的,但我从不揭穿;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利用价值,但你从不点破。
“面子”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日常交往中的社交货币,其价值由交往的双方在每一次接触的互动中动态确定。“面子”是无形的,它是一个人在他人心目中的言语、行为、实力、修养等印象总和。但“面子”又是非常具象与物化的,一旦一个人失去了“面子”,他将在内心感到失去社会曾附加于他身上的所有。翟学伟认为,“脸是一个为了维护自己或相关者所积累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圈内公认的形象,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表现出的一系列规格性的行为”,“面子是个体对做出的脸的行为后的自我评价判定及其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脸面”一词在日常社交环境中一直处于黏连、融合状态,“脸”是行动的结果,而“面”则是感应的结果。
作者提到在一个小区微信群内需要踢出一个经常发送群信息对群友造成不适的人,他们不是正面冲突或直接踢人,而是找到了一个即将离开本群的年轻群主,让他以情理之中的原因解散微信群,从而达到将该人屏蔽出去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假如是在线下发生类似的事情,缺乏智能手机所支持的一种曲折但有效的人际处理手段,那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我曾想起在疫情后期,一位小区内的文革一代老人每天都在小区微信群内发送自己撰写的诗词,但很少有人回应。突然的某天,这位老人言辞恳切地说“为了维护本群的日常秩序,加强管理,现在我邀请本社区居委会**领导加入本群……”结果我瞬间看见有多人退群。可能如今随着数字化与平台化发展,我们已很难真切体会到“组织”对一个人命运发展的重要性。而我从小区的那位老人身上却真实感觉到其对“组织”的渴盼,或者说,“组织”的存在与否,决定了文革一代老人的身份政治——即“我是谁”。
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位被踢出微信群的老人,被踢出群后,这位老人寝食难安、羞愧难当、惶惶不可终日。在他心中,离开微信群即“离组织”,而“脱离组织”是一种严重而残酷的集体记忆——它意味着自己将失去一切,成为社会所排斥的边缘人。所以当他重新被拉入微信群的时候,那种狂喜是我们所不能体悟的。将文革时代的群体记忆与个体经验重新实践到数字革命的进程中,这或许是每一位老人在数字时代的“自我革命”。
一提到“革命友谊”,可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并肩作战、浴血战场等画面。而当一个老人通过微信找到一位曾经一起下乡插队的朋友,他首先想到的是“革命友谊”,这种来自青春期历经苦难后的“重逢”,除了互诉当年下放农场的“峥嵘岁月”,似乎没有其他可以充分表达情感的内容。而和平年代的“革命友谊”似乎变得更为轻逸,一起工作,一起打牌,一起游玩,似乎都被不自觉地称为“革命友谊”。数字时代的“革命友谊”已泛化为一种共同记忆的经历,它与过程的艰辛无关,仅代表一种共同的时间见证。
对于老人而言,基于智能手机的数字社交,并未取代日常的真实交往,而是将微信以及朋友圈这种可控的、灵活的社交模式,作为“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通道,为日常交往中说不出口的、冒昧的、突兀的请求提供压力纾解渠道,为请求的顺利达成注入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润滑剂。
特别是对于讨好型人格或处于社交劣势的人而言,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似乎可以低成本但又高效地达成交往目标。比如你可不必始终保持微笑地倾听对方讲述你并不感兴趣的话题,而可以用表情包更为丰富的内容来表达和传递更多隐藏的涵义。“表情包”并不是将“表情”进行廉价化、虚假化地实现,“表情包”的功能是在快速完成多人社交过程中达成一种情感上的心理平衡,没有人会被冷落,没有人会被忽视。而这正适合文革一代老人的内心诉求,毕竟,“不要得罪任何人”有时是他们用尊严甚至鲜血换来的认知。
在作者的叙述中,“门内”即门后的空间,象征着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原则,而“门外”则与一系列面向公众的行为准则有关。而智能手机正在为老人提供一种“门外”时刻的可以“宾至如归”的地方,一个便携式的“家”与舒适区。当他们在外面感到不适时可以随时撤退。所以,当我们看到有机构调查国内年轻人平均每天掏出智能手机或点开手机屏幕的次数时,我们这背后并不仅仅是数字环境下的用户习惯,而是一个国家或族群的精神状态。智能手机成为一种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屏蔽所有可能的社交不适症。作者指出,“智能手机的使用在老年人认为‘出去’的必要性和他们渴望‘在家’的舒适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智能手机不仅塑造人的认知、记忆,它还塑造人的身体与精神。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将身体特征与服装在“时空错置”下进行重现。当问到文革一代的老人为何喜欢穿着鲜艳地拍摄手机照片的时候,他们表示自己年轻的时候衣服只有黑色灰色蓝色,而现在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颜色,他们不想失去选择的机会。
对于那一代老人而言,智能手机正在成为一种比“红宝书”更灵验的物体,它不仅在横向联结我们的人际关系,纵向修补我们的时间记忆,它还在重构“亲近”与“疏远”之间的距离感,重构“平行”与“交叉”之间的关系。
或许,智能手机对于一个特殊的老人群体而言,它是一种现代化进程对历史令人失望之处的补偿机制。
无处安放的“革命激情”与数字社会的“主人翁”
年轻时代的经历让文革一代老人的自我认同始终徘徊在一种“未满”的、“不合格”的状态之中,他们被教育只有在不断的“自我改造”中才能成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新人”。在他们的内心,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边远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一种“自我改造”。(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数字革命浪潮中,不断要求自我学习拍照、修图、做表情包、发朋友圈等,也是一种“自我改造”——直至成为数字时代的“新人”。
生理上的衰老与心理上因怀旧而起的蓬勃生命力,在智能手机的数字技术感召下,逐步释放了文革一代老人内心无处安放的“革命激情”。而作为“数字难民”的一代,这种“革命激情”的存在让他们进行自觉地“自我改造”,以追求做“新人”的革命理想。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想做新时代的退休金消耗者,他们要做的是“数字社会的主人翁”!
文化大革命的“新人”与数字革命的“新人”有什么异同呢?他们同样被一种伟大的愿景与理想所诱惑,而不同的是,前一种“新人”在宏大理想幻灭后而失去意义感,而后一种“新人”却不断地被算法和网络给予的正反馈中持续地满足,持续抬高自身的预期。他们会去参加老年大学组织的专门的手机摄影班学习手机拍照,会去组织专门的红色旅游回来后撰写游记发到“美篇”App,他们甚至还会在年底组织微信群“春晚”,以歌声、乐器和舞蹈来表达自己无愧于这个数字时代的发明。
作者认为,正是智能手机革命使这一代老年人成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完整经历了两次革命(文化大革命与数字革命)的社会存在,也是智能手机革命赋予了中国老年人在人生的晚些时候追求个人抱负的力量。然而,正是直接源于共产主义革命的自我改造理想,赋予了老年人以热情参与和认同智能手机革命的动力,而不是将其视为排斥他们的青年革命。正是智能手机在社交、购物、娱乐、服务等场景中与老年人的交互,从而让智能手机成为“当代中国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的重要文化实践场地”。
在公园、在餐厅、在酒店、在高铁……我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文革一代的老人开始用智能手机记录自己的生活。作为年轻一代,我们用自己对数字革命的认知来鄙弃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方式。我们调侃和揶揄他们的智能手机使用氛围——从手机铃声、微信头像、微信群信息到朋友圈腔调。他们表现出对进入数字时代的出奇热情,而当代年轻人却以圈层隔离地方式无视或漠视了他们进入新的革命时代的努力。而当这种漠视正常而名正言顺地发生之时,我们将不无遗憾地意识到:无视他们在数字空间的存在,就是无视那段历史的存在。
或许正如作者所言,“经济改革带来的物质享受不一定能解决毛泽东时代‘生活目的’宏大叙事破灭后留下的幻想破灭问题”。那么,数字革命的“使者”智能手机在老人退休后的丰沛的个人时间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一方面,智能手机为每个经历了宏大叙事破灭后留下的空虚感与孤独感提供了一种修复幻象、重塑梦境的即时性工具。另一方面,基于智能手机的社交、娱乐、购物等应用通过持续填充老人们的空闲时间,从而让他们从“有事可做的忙碌”转移到“无所事事的忙碌”,并在与智能手机的应用互动与社交网络中暗示他们仍然是一个“有用的人”。
除了“自我改造”与做”新人“的集体记忆延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思想,孝悌文化通过短视频播主正在对老人进行轰炸式覆盖,成为老一代人教育新一代年轻人“发扬传统”、“遵守孝道”,做“旧人”的方式。他们不会明确地教育你如何“做人”,但他们会将“孝道”、“中医”、“人情”等短视频不定期转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微信群,而伴随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什么食物一起吃可能“中毒”的视频、诈骗链接等在群内蔓延。
每个人都有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微信群,这可能是智能手机时代最为奇特也值得研究的数字人类学景观。
在上个世纪,他们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所感召而走向农村与基层,通过在枯燥的劳作中寻求“自我改造”的可能性,今天看来是“下放”,而那时的语境是“在革命的烈火中锻造自己”。当数字革命浪潮中的智能手机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一堆可以自由选择的选项中继续了六十年前那些尚未完成或未找到答案的人生命题,只是激情依然,但在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的时代,再没人告诉他们唯一的正确答案了。
“他们并不后悔过去的选择,他们主要后悔的是,年轻时,他们根本没有选择。”在这个充满了选择的数字时代,那一代老人的生活理想比当初更为坚定,还是更迷惘?无人知晓。
结语
在技术媒介叙事中,智能手机是“人的延伸”,是”人体器官“的一部分。《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Urban China》似乎要告诉我们,智能手机是文革一代老人的“青春副本”,只是这个副本不是留在时间里,而是从未来到过去进行洄游——从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开始一点一点恢复出自己的青春模样。
智能手机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就像一种现代精神生活的象征与寄托的容器,每次点亮屏幕就能获得些许抚慰。智能手机既是自我的,又是公共的,我们通过密码、防窥膜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将他人隔离在我们的手机安全距离之外。但是,我们又通过朋友圈、微信群、晒网购图、自拍等手段来最大限度地公开展示我们的生活。智能手机既是外在的,又是根植于内心的,我们愿意公开展示的所有信息、图片和视频,其实都站着一个默默地隐于背后的自我。
对于上海文革一代的老人,智能手机究竟意味着什么?当那个时代旧的记忆挥之不去,要么成为伤疤,要么成为勋章,而新的记忆与经验正在被数字革命一点点重塑,当这两种记忆和经验叠加之后,新的时代烙印正在形成——他们既要在缅怀过去的时光中或忏悔或迷惘,又要新的革命进程中奋起直追不能松懈。显然,这些都是与这个追求“躺平”的时代格格不入的。
作者写道:
老年人不仅庆祝他们当代的生活,作为对过去的否定,这种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拥有更多选择自由的可能性。他们也在努力让自己承认,在回顾过去时,他们记得“规定的生活目标”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即使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夹杂着对过去的怀旧之情。
文革一代的老人始终被革命精神与情怀所激励,数字革命又让他们重燃了对年轻的某种生命热情。所谓“革命人永远年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给予一个老人以生活的希望了。
我记得某次在上海浦东机场登机口候机,检票开始后,当一个老人带着自己的孙女冲向无人的“公务舱”登机口时,她的女婿就在旁边和她的女儿大声讨论“你看你看,就是他们这样的老人喜欢耍无赖不讲规矩,因为他们是红卫兵的一代,他们年轻时候就喜欢瞎搞……”我当时在想,如果我是那个老人,我应该不会把女儿嫁给他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