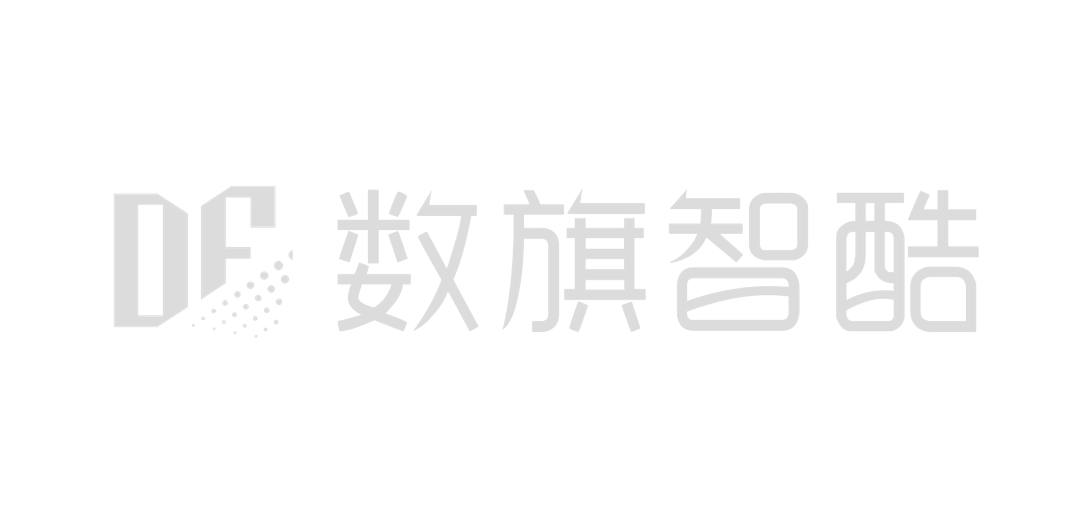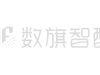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本文为对深圳福田“AI公务员”的研究评论
日前,深圳福田区推出了基于DeepSeek开发的“AI数智员工”,并已上线11大类70名“数智员工”,覆盖了包括公文处理、民生服务、应急管理、招商引资等在内的240个政务场景。这一案例被媒体称为“AI公务员”。
从“数字哨兵”、“数字人”到“AI公务员”,在数字化的发展历程中,建立技术与人的关系,对技术的感知和想象进行“拟人化”,不仅意味着人类对技术能力与发展水平的评估与认可,同时也隐含了人类对自身进化速度、生存价值与发展愿景的忧虑。
AI和公务员,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本身就显得魔幻与冲突。AI是时下热门的技术概念,代表着革命、颠覆、创新、破坏以及超越等系列价值指征与意义载体,而公务员则是现代官僚系统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和符号,也是官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所以,“AI公务员”本身就意味着一组秩序与反秩序、系统与超系统、基因与转基因之间的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AI公务员”的提出的确代表数字政府生态的一个“新物种”的出现,移动时代的信息流模式开始逐步转向AI时代的任务流模式,而政府机构的“部门+岗位”的原始结构也将向“能力单元+任务集群”的生态结构转型,它将一个全新的课题摆在了现代行政系统的面前:相比于平台时代的数字技术作为“他者”的角色,AI技术可能正在以非物质的方式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它可能与公务员在未来是辅助、驯化、依赖或共同进化等任何关系,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关系就非常关键。
个人认为,关于“AI公务员”的讨论至少三点认识是需要厘清并形成共识的。
一是“AI取代公务员”是假问题但遮蔽了另一个真问题。
围绕“AI公务员”,行业和媒体热衷关注与报道“AI是否会取代公务员”的话题,这种耸人听闻的腔调掩盖和遮蔽了背后的严肃问题,即当AI大规模介入和应用于政务办事服务流程、社会治理场景,由于数据集的采纳与标注问题以及以往数据中的固有成见或“惯例”,会对社会公平、行政伦理等产生何种影响?我们期待的那种“没有感情色彩的公平”、“消除徇私舞弊的空间”真的会出现么?这才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真问题。
而对于公务员相关岗位的所谓“取代”是一个漫长遥远且不只是与技术有关的过程,如果按照《技术陷阱》一书中的观点,它会涉及到制度设计、社会基础、工作程序、考核度量等都需要重新设计。所以,我们可能不应该担心公务员,而首先要担心的是我们自己——未来面对政务系统的“AI公务员”该如何自处。
如果说AI在政务领域的应用场景就可以称之为“取代公务员”,那纯粹就是一种假象,只能说明这些场景在以往的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就在被持续优化或更新工作方式,而现在只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高能级AI提供了一种貌似让人更高更快更强的感知与想象,而这是并非事实。
二是场景数量是不是一定就等于赋能价值与效率高低本身?
这是一个很不讨好的发问。因为长期以来在数字化领域都有一种将场景量级等同于数字化价值本身的心照不宣的论调。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必然需要在场景中体现价值,但场景的存在并不必然等于数字技术发生了预期中的价值。这是两回事。如果回到数字政府领域,我们可以想想,当年将一个事件拆分为N个事项来拼数量以证明上网政务服务事项数,这体现办事服务水平了么?而将网上办件率、热线接通率、事情办成率等拉通到99%的小数点后两位数,又是否可以真正反映公众的办事服务质量与体验本身呢?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是,当碎片化的场景太多是否对效率和体验本身已无法形成赋能而将走向反面呢?如何去平衡这种矛盾?围绕AI技术进行预先规划设计的场景与真实需求之间是否存在应用鸿沟?如何去识别和调试这种鸿沟的存在?
三是智能机器的“监护人制度”应该监护什么?
深圳福田区称针对“AI数智员工”(AI公务员)在全国首推“政务辅助智能机器人管理办法”,以政府采购、使用的政务辅助智能机器人的全流程管理为主线,构建伦理框架,明确了技术标准、应用范围、安全管理以及监管要求,推动AI技术在政务领域的合法合规应用。
如果我们称之为算法的“监护人制度”,它设立的初衷是确保机器的安全性,还是保障工作者及服务对象的权利?在算法那个不可见的“黑盒子”里,我们可能最需要关心的不是盒子里到底有什么,而是我们在日积月累的日常工作中因为政治、价值观、社会实践等形成的固有成见,以及我们所在的系统与制度环境所赋予我们的视野和价值认同。我们以何种方式来关注和消解那部分可能存在的“瑕疵”?这很重要。
算法推荐的本质是“多数人的选择”,而“沉默的大多数”、“多数人的暴政”等多是基于“多数”产生的。当碎片化的算法被合成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措施甚至制度,并将算法制造者、训练者、决策者以及受众进行物理隔离,相互看见也听不见,我们应该如何去识别算法的选择是代表“民意”还是加速“极化”?在日常的政务服务或社会治理场景中,如果算法将多数人的选择以委婉、艺术的方式设定为“正确选择”或“唯一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抵抗?或者谁可以有抵抗的权利与能力?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人”的定义是被历史、政治和社会不断建构的。而人与机器的关系也是如此。2007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科学技术人类学名誉教授露西·萨奇曼指出,“记住,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的,特别是以历史的方式,具有特定的社会和物质后果”。所以,讨论“AI公务员”的未来都应该建立在我们如何建构人类与机器的界限之上。
“AI公务员”介入政务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授权与无法问责。我不相信人们会慷慨地与机器分享自己的权力,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机器在数据轰鸣声中无声地剥夺了我们对问题的定义权,并让我们信以为真。
《纽约客》在2025年2月1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埃隆·马斯克的人工智能驱动下对人类自主权的战争》的文章,我摘录内容如下,与深圳福田“AI公务员”无关。
实际上,联邦政府突然间像一个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一样运作;马斯克,一个未经过选举的亿万富翁、飞行汽车和火星旅行的指挥者,把美国作为他最大的实验场,测试这种未经验证、未经监管的新技术。他并非唯一一个将人工智能塑造为社会救世主、带来乌托邦时代效率的推动者。
由人类管理的政府本质上是谨慎且缓慢的;机器自动化版本的政府将变得快速而冷酷,减少对人类劳动和人类决策的依赖。
随着这些员工被禁止进入办公室、工作电话被停用,一个新的、不民主的“深层国家”正在填补这一空缺:一个由机器和设计这些机器的小精英所强加的系统。通过DOGE,马斯克不仅在边缘化国会并威胁违抗法院的命令,帮助国家走向宪法危机的边缘;他还在联邦官僚体系中悄悄引入了一个新的极权政权的种子——由聊天机器人驱动的科技法西斯主义。
当然,科技企业家所认定的进步,并不总是与更平凡的集体福祉的理解相符合。马斯克在白宫的位置,可能会让我们意识到,社会网络中的颠覆更容易被接受,而我们的社会保障金却不那么容易接受这种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