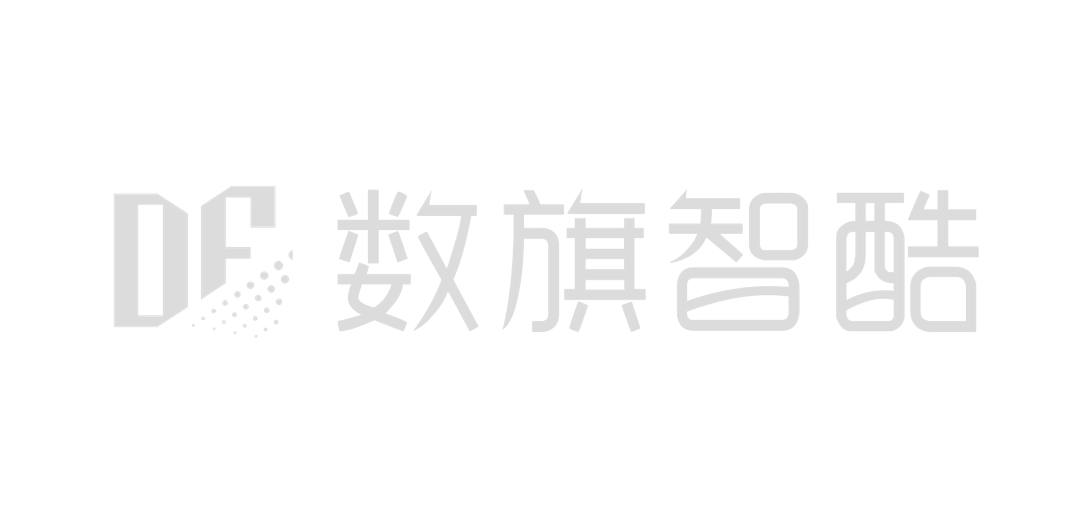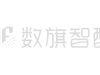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佛山市顺德区江义村宣布将DeepSeek接入“智慧乡村平台”,说是全国第一个接入DeepSeek的村级行政单位,这在全国政务系统争相接入的当下,多少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一个面积4.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500人左右,村集体总收入4861万元(2023年)的村子,它的乡亲们比北上广深杭的牛马们更需要DeepSeek来磨豆腐么?在公众舆论中被描摹得越抽象、摩擦得越光滑的DeepSeek,与具体、混沌、充满生机的社会发生碰撞时,它被视为一种新型的“数字万金油”。
针对广西某县委书记要求基层干部至少掌握使用两个AI应用的新闻,《半月谈》微信公众号于2月22日发表了题为《基层,不妨大胆拥抱AI》的评论,文章认为,基层重视AI,是一次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有益探索,但转变思维比升级技术更为关键,基层干部需提升驾驭AI的能力。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曾于2024年1月的《中国新闻周刊》一次采访中表示,“要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就不要急于在基层推行数字化”。
数字治理的实施是来自顶层设计的意志,对于基层治理工作者更多是以任务压力的方式进行呈现和传递。因为基层的很多工作都强调接地气,具有突发性、灵活性以及模糊性等特征,以量化与颗粒化为特征的数字应用无法准确把握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与条件。所以,在DeepSeek浪潮之下,基层单位与部门该如何应对、选择并吸取移动政务时期的教训就十分重要。
将DeepSeek引入智慧乡村平台,本质上是对“✖️✖️大脑”叙事的一种延续,是将城市级的数据应用与服务能力缩放到一个最小的社会管理单位中。这样的问题在于,为了体现数字赋能的价值,用户需要不断去适应技术造成的困惑、障碍以及不合理要求,最后成为机器可识别、数据受认可的那一部分。
对于在数字化洪流中被裹挟前行的基层工作者与公众而言,他们因为缺乏数字素养导致无法完整享受数字红利,或因缺乏数字化操作能力而在日常乡村治理工作中倍感压力,DeepSeek作为一种效率辅助工具的价值是真实存在的;而对于一个不断变化难以把握并附庸了熟人社会中海量隐性知识的乡村现实而言,用精确的算法模型与“被定义过的数据”来规范和干预每一个村民的日常生活,用数据去量化无法计算的悲喜、品格以及道德,我们对技术的期待是什么呢?
DeepSeek究竟对村民有什么价值?会成为类似于抖音或微信一样的存在么?我们所设想的是村民可以随时获取对村规民约、政策文件以及政务办事的了解,而一个以道义、良心以及脸面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熟人社会,这些对于村民重要么?或者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需求么?
乡村的现实是,那些出口成章的人并不一定能写一手好文章或问出一个文绉绉的好问题,那些善于处理邻里纠纷摆平乡间利益纠葛的人,他们更多的不是因为学富五车,也不是因为懂法用法,而是依靠常年累月沉淀下来的街头智慧和对世故人情的洞察。据说DeepsSeek很会“看人脸色”,会根据提问人的毕业学校来告诉你“到底是清华好还是蓝翔好”。那么,DeepSeep会如何建议去一个村民家吃席包多大数额的红包么?会怎样建议你去跟邻居较量一块在30年前就没有权属定论的宅基地?
基层治理工作是有泥土气息的,是在繁复、细碎与混乱中进行的,基层百姓的某些真实诉求不会是那种可见性很强的数据,而是以暗示、比喻、旁敲侧击、讨价还价等各种他们擅长或拿手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的真实心声袒露在治理者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可能不是DeepSeek的赋能价值,因为就档案管理、信息查询、政策问答、办事指引等事务性常规性工作而言,效率提升的价值不证自明。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DeepSeek进入到乡村治理场景,这样一个自动化的工具全面进入基层治理者的日常工作,算法越精准,工具越好用,那么,“党群服务中心”的党与群的距离到底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基层工作者面对一个对工作内容娴熟的智能体是不是比面对一个语焉不详或者死缠烂打的村民更让人舒心?AI工具的应用又是否会让人想当然地从“减少不必要的走访”到连“必要的走访”也依靠智能机器问答来解决,因为对技术的信任告诉你:智能助手比你了解乡村更全面,村民想说的,智能助手基本都想得到。
此外,类似于DeepSeek数字工具的使用,极有可能带来基层减负及“指尖形式主义”的悖论。原来因为数据采集、信息报送的复杂与重复,以及面对多个政务App、小程序的无效打卡与数据注水,此类现象的存在让基层减负成为舆论焦点。而DeepSeek等工具对日常报表的效率提升与材料草稿的快速生成,这是否会导致那些被归于“数字负担”或“数字形式主义”的事务会变本加厉地成为日常治理流程中的一部分,因为反正是由机器来完成(或机器辅助完成)。
我们不断探索用更先进的数字化工具来消除数字形式主义,而工具应用能力与效率的提升让数字形式主义事务成倍增长,这就是数字形式主义的悖论。我们为了维持人类对技术的价值边界发掘,进而阻止了自身对工作本身的意义确认。当工作的价值被数据支配、被算法抽空之后,工作自然会变成无意义的“狗屁工作”。
有新闻报道称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为中国游客批量定制“网红景点”,以满足中国游客的打卡需求。而《Filterworld》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并不是简单因为这个地方风景漂亮,还因为它的历史、带给人的想象与憧憬、在人生经历中留给人的记忆以及对奇遇和未知的挑战。而以数据和算法推到游客眼前的网红景点,不仅将破坏人对景点的想象,还对当地生态和社会造成巨大压力。“过度旅游”让需要依靠人的感知和探索的景点因为要在数字世界留下痕迹而被摧毁现实体验。
“过度旅游”让我想到“过度治理”。当我们发现一项工具的能力边界超出了以往的认知,于是我们希望不断探索其能力边界,总想在更多的场景中展示其价值,从而导致“过度治理”,数据与算法使得现实世界逐渐失真,使社会治理原本不被视为“问题”的被蓄意或因为技术可及性而成为一种被制造的新问题。这或许是我们应对AI技术介入基层治理应该保持谨慎的原因。
在一个被“留守儿童”、“养老保险”、“生态环保”、“基层选举”、“农村彩礼”等复杂社会议题环绕的中国乡村,那些已经或正在准备接入DeepSeek的“智慧乡村平台”,会成为基层治理工作的效率神器?抚平公众情绪的按摩棒?还是社会撕裂的加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