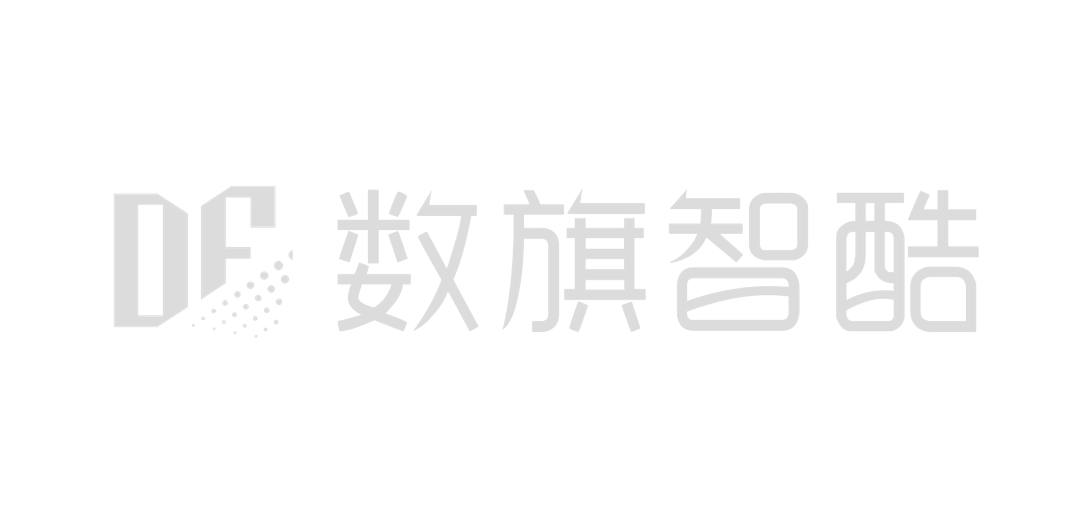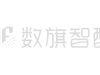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2024年4月2日,国家数据局发布《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导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距离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已有十年时间。从2015年提出的“互联网+”到2023年的“数据要素×”,智慧城市发展的背景、条件以及愿景已处于新的历史坐标,而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叙事也被重新塑造。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围绕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数字服务、产城融合、生态环保、数字应急等多个方面做出了部署安排,并提出,2030年,全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全面突破,涌现一批数字文明时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结合对智慧城市发展的长期观察,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跟踪研究,数旗智酷针对《指导意见》做初步解读与思考如下——
01.如何重新定义智慧城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首先,智慧城市不是城市发展的“目标”,而是推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杠杆。特别是在后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发展愈发扑朔迷离,城市作为前沿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应用场域,当大模型、元宇宙、区块链等新技术与新模式逐步渗透城市运行细节,城市发展的空间约束、想象空间与区位限制的天花板被逐步打开,在数字文明时代,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成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新坐标。
其次,验证智慧城市发展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中国经验”。《指导意见》中涉及了浙江、上海等地方和城市在过去几年持续探索的数字化改革与发展经验,特别是“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处置一件事”、“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基层数据回流机制”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响应与推广,以具体改革措施为抓手,继续深化智慧城市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城市创新经验的溢出效应。
再次,进一步认识数字经济与智慧城市的关系。《技术的本质》一书指出,“经济是技术的表达”。城市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技术域”的创新应用与价值涌现,本就可以视为数字经济的一种表达。而如果从全国重要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能力与水平来看,以上海、深圳、杭州等为例,一方面,以腾讯、阿里巴巴、拼多多、小红书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创新企业涌现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新模式、新业态以及创新人才储备;另一方面,城市在经济、生活、治理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加速,通过政务服务、社会治理、市场监管等创新打造高质量营商环境,可持续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第四,“结果导向型运营”成为智慧城市可持续运营的价值保障。智慧城市运营的对象与核心发生变化。如果从智慧城市发展的进程来看,未来智慧城市的运营将从系统运营、平台运营、服务运营转向数据运营,由封闭化的、线性的、单极化的运营模式,逐步走向生态化运营。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下,未来智慧城市的运营将变得日趋复杂,在数据产权、流通、使用加工以及收益分配等方面都将面临挑战。从有PPP项目融资标的逾期引发的金融风险到个别城市将公共数据资源“打包售卖”的奇闻,再加上数字经济平台公司在“平台资本主义”语境中无法脱身的“数据歧视”嫌疑,因此,市场化与社会化融合、商业性与公益性叠加的智慧城市创新运营模式亟需探索。“为效果付费”不仅是地方城市财政“过紧日子”的选择,同时也是城市市民用户口碑的价值取向。
02.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四个关键词
一、韧性安全
韧性城市具有抵御风险能力、自愈恢复能力、适应能力等特征,数字技术是提升城市服务弹性与治理韧性的重要手段。在极端天气频发、城市安全应急形势严峻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事故导致的城市运行风险等成为现代城市亟需应对的挑战,要防止城市的“数字脆断”和防范城市运行的系统性风险,需从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角度来统筹规划城市“韧性安全”发展路径,评估城市数字化转型阶段、能力与质量,面向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数字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存量与创新增量等,在城市数字生命体征之外打造一套抗风险、快恢复与高自愈性的“数据化生存屏障”。
二、适数化
《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城市开展管理服务手段、管理服务模式、管理服务理念的适数化变革”。构建适合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制度规范,从来都是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艰巨任务。移动一个按钮、更新一条信息、修改一项流程等,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系统、平台和应用中都是极为简单的工作,但是由于涉及到部门利益、安全风险等问题,其操作的难度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与理解范围。“适数化”的过程本身就代表了权力流程与数据流程的博弈过程,用户思维与行政思维的切换过程。
三、数字更新
“城市更新”的主要路径一般涉及两个方向,一是拆新换旧实现土地价值转换,比如地产时代的“拆迁”;二是实现功能改造与价值创新,比如通过功能设计和意义植入实现文化唤醒、产业焕新。那么,城市“数字更新”的关键是什么?《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城市“数字更新”,加快街区、商圈等城市微单元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探索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消费场景,激发产城融合服务能级与数字活力。即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内容等来提升传统城市基础设施的便捷度、应用效率与创新场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更新”绝非将旧电话亭改造成为一个使用起来极为别扭的“一键叫车”平台或查不到具体信息的“游客信息亭”。“数字更新”跟城市发展需求、街区资源分布、社区人群结构等息息相关。
四、数字经济就业吸附力
当前的城市招商本质上已进入存量竞争时期,城市的大型数字化建设项目承接方本身就承担着推动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的重任。《指导意见》提出,“加速创新资源共享助力以产促城,发展虚拟园区和跨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增强城市数字经济就业吸附力”。对于就业而言,数字经济至少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不同的就业人群可根据各自的技能优势进行远程工作,比如对于内容审核业务的异地外包;二是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可以推动生态链的延伸与扩展,比如直播带货催生物流、选品、生产、营销等链条的系列变革。因此,通过打造虚拟园区与跨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可以发挥数字经济的辐射效应与集聚效应,推动人、产、城的融合互动发展。
03.未来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几点可能性
一、大模型将改写智慧城市的发展逻辑
有一句业内的调侃叫”现在建设智慧城市还搞大系统大平台约等于四九年加入国军“。ChatGPT、Midjourney、Sora等大模型应用的出现不只是信息服务与内容产业层面的变革,基于AIGC的城市治理、服务、营商、生活等也将发生巨变。可以想见的是,围绕自身在城市的需求和身份打造一个专属的”City Agent“ ,以扩展对城市数据的利用能力与价值发掘能力,这将成为AI时代城市生存的重要选择。随着大模型基于数据、经验、知识的训练,对城市物理空间、运行逻辑、发展伦理的感知越来越深入,那么,城市在规划、决策、交通、应急等方面的成本与效率也将锐减,基于推理和涌现,大模型可以支撑城市更敏锐地感知、诊断和预测未来。如果超级App是移动时代的城市服务入口,那么CityGPT可能就将是智能时代的城市服务入口。总之,大模型不仅将改写过往搞大系统大平台忽视运营效率与体验成效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同时可以主动发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诸多可能性,在数据开放共享、数据建模、应急预案设计等方面提供全新的应用思路。
二、优质应用场景就是城市数字化转型关键资源
城市数字化转型场景来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过去几年已有不少地方以开放城市应用场景清单作为数字产业招商的政策选项。毫无疑问,当政务、治理、文旅、制造等都值得用数字化方式重做一遍,开发城市数字应用场景就是重塑城市数字竞争力与重新发现城市腾飞新曲线的方式。对于数字经济平台企业而言,城市数字应用场景构建是一种模式探索与增量,对于数字经济创业企业而言,则是一种生长机会与竞争力打磨。如果要举例的话,娄底新化的印刷产业与盗版书”畅销“全国,这是一个治理场景;江西上饶的“民宿提灯索赔”事件,这是一个文旅服务场景;上海从早教中心跑路到月子中心跑路,这是一个监管场景。评估一个城市数字应用场景影响的人群、行业及关键环节,以数字技术去理解、改造和提升运营逻辑,就是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新机会。
三、隐私安全是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底线
隐私问题一直是城市数字化转型不可忽略的关键问题。健康码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对隐私保护的关注与监管部门的重视。但是,围绕个人隐私信息的“灰产”链条依然没有根除。比如高铁卫生间人脸识别取纸、扫码点餐获取个人信息、小区/办公大楼刷脸过闸以及快递驿站成为个人信息泄漏重灾区……因此,深化智慧城市发展不仅需要深化对智能技术的应用、服务体验的提升、治理逻辑的优化以及产城融合的创新,还需要深化对公众和企业的数字人权的保护,建立智慧城市对个人数据采集和应用的规范机制。凯文·凯利在其新著《5000天后的世界》中提出,通过“个人数据信托”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个人数据的流通、应用和收益权利进行管理,这或许数据产权发展路上亟待探索的方向。
四、提升数字素养是获得进入数字文明时代的门票
近年来发布的多个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相关文件,均要求构建与数字化发展要求相匹配的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专业团队。面向当前智慧城市发展与城市数字化转型,要深化城市管理部门与管理者对数据素养、前沿技术的认知与使用能力,比如如何利用生成式AI提升自身工作绩效,对于数字应用场景与现象具有基本的判断力,对网络舆情处置具有基本的常识与原则等。此外,还需深化公众和企业对数据价值、数据安全以及数据保护的认识。《指导意见》提出,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探索建设基于城市统一标识体系的“城市码”,推进房屋建筑、重大项目等“落图+赋码”机制,形成“多码合一、一码互联”的服务治理体系。因此,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将从超大城市、市中心向城中村以及城市边缘扩散,逐步渗透到不同层次人群,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以应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冲击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