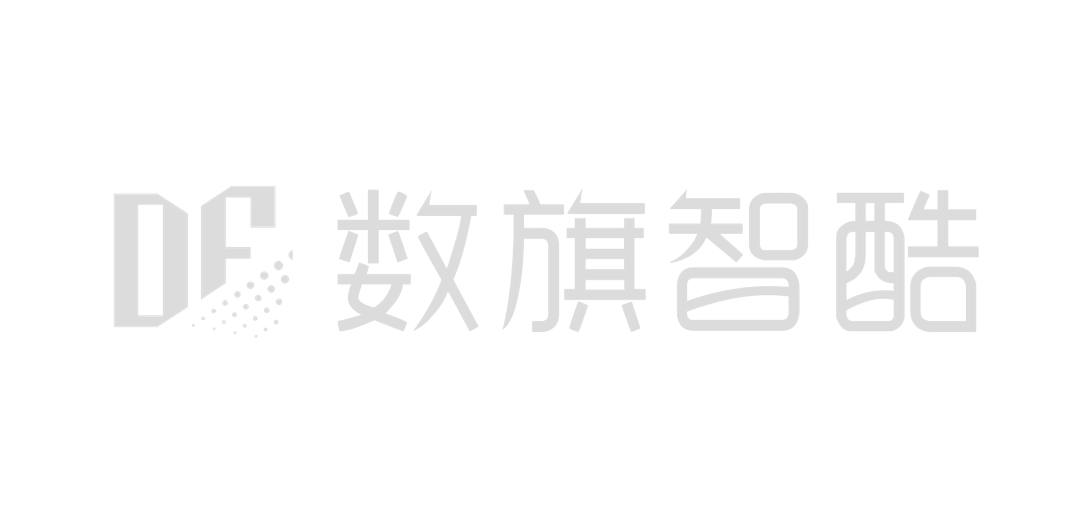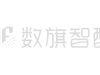2023年11月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北京服务”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了打造“北京服务”的“六大环境”与“八大行动”,作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与营商环境资源洼地优势的北京,此番举措不仅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大环境下彰显了以数字化、智慧化驱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决心,同时也代表了未来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升级方向。结合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与营商环境优化的现状与趋势,笔者认为“北京服务”的提出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九大思考方向——
01.
从《意见》的词频分析来看,“制度”一词出现了36次,虽然在政务服务、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智慧城市、数字社会等均涉及数字技术的应用,但核心还在于政策的制度化供给,强调政府行政管理、政务服务以及营商服务的制度、规范与标准化建设。法治化应是推进数字政务服务与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与前提,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数字化与法治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嵌、互文的关系,作为公众和企业需求呼声较高的数字化改革突破,需要法治化规范并保障改革成果,在营商环境与政务服务的法治化推进过程中,需要数字化来支撑“同样的法律、同样的执行”,以规避可能被放大的“自由裁量权”。
02.
从过往研究来看,数字政府建设曾被视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手段、内涵与驱动力。因此,北京此番提出“以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数字政府为主抓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服务型政府”与“数字政府”、“数字”与“政府”的关系。“服务型政府”曾经是与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等一同作为政府建设目标的,将服务型政府与数字政府并列,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笔者认为,此处应该强调的是制度变革与技术赋能之间的协同,强调科层制政府运行与扁平化数字政府改革之间的平行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03.
北京优化营商服务与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版图范围、占据位置与需观照的关系是什么?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是上海推进数字政务发展的基本盘,而北京的政务服务基本盘是在“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与“北京+雄安”的层叠之中,涉及到央企与部委、地方与中央、中心与副中心等诸多关系,不同区域与行政主体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区隔与资源落差,所谓的“跨省通办”、“政务服务同城化”是否可以像长三角一样通过“飞地模式”解决?“北京服务”始于北京,但不可止于“北京”,能不能构建一个以“北京效率”、“北京标准”为带动的营商环境生态与政务服务跨域联动模式,这可能才是“北京服务”的意义所在。
04.
提升政策的可预期性与通达性应该是近年来每个城市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无论是免申即享、即申即享还是无感申办,其核心都是通过数字技术来提升政策的供给能力与获得感。从数旗智酷调研的全国 GDP30 强的城市情况来看,打造“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覆盖政策服务产品或建设独立的“政策服务平台”基本成为标配,而将政策服务与人才、中介、金融等服务进行连接,则考验政府的资源组织与协调能力。因此,北京提出“加快推进全市一体化政策服务平台建设” ,应该着力于打造“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数字经济、消费等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的政策服务产品,为目前以智能技术驱动并逐步呈现内卷化的政策服务创新提供战略视野与产品思维。
05.
“城市大脑”、“产业大脑”、“社区大脑”等成为过去几年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数字治理等领域被普遍接受的叙事,其核心在于放到了“大脑”的“数据即智慧”的想象,但忽略了组织运行与任务执行过程中的非技术因素。《意见》提出,“打造智慧服务、高效监管、科学决策于一体的数字政务服务大脑。”数字政务服务大脑本质是将政务服务的决策者、管理者与运营者的行为与流程协同的指挥中枢。与其他大脑不同的是,政务服务是一个有边界、有标准、有底线的领域,数字政务服务大脑要的不只是政务服务的创新洞察,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数据对流程再造、机制革新的反哺价值。
06.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崛起,给政务服务创新带来了诸多可能性,也一扫“人工智能+政务服务”过去多年的沉寂与尴尬。《意见》提出的智能审批、在线导办、智能咨询等均是当前条件下“人工智能+政务服务”的经典应用场景,审批的辅助办理、“数字人+大模型”的在线导办以及人格化、持续性对话式咨询,这对未来提升政务服务的供给能力、体验度与获得感均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作为大模型的发展重镇,拥有文心一言、智谱清言、百川智能等领先的技术流选手,北京推动“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无论在算力供给还是服务创新方面都应该担当起AI大模型时代的政务服务创新使命。
07.
《意见》提出,“提高政策可预期性,依规依法履行涉企政策调整程序并根据实际设置合理过渡期,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一致性。”对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在线教育、中介租赁、共享经济等领域过去几年的“踩踏事故”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估计全国乃至全球也少有城市能体会到北京的“痛”。因此,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不仅要关注政策目标,同时要对社会舆论、企业意见以及相关部门的监管服务取向有更为深刻清晰的洞察,基于数据与广阔视野的系统监管和协同监管不只是一句空话,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对政策落地的推演与模拟,或许可能应该成为政策设计的重点环节。
08.
《意见》提出,“结合本市实际,针对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涉及的外部因素和条件,设计能够综合反映本市营商环境水平的评价指标,构建具有北京特色的营商环境指数体系。”营商环境评价与政策设计,与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政务传统、产业结构以及未来愿景等均具有强相关性,当然也不可将一个千年古城与一个新兴城市进行类比,更不可将一个人口和 GDP 刚破百的城市与万亿超级大城进行类比。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估出现“中途暂停”,其背后的困境应该就在于数据感知与企业感受是存在“温差”的。也就是说,数据并不反映企业的真实感受,对数据指标的优化并不改善营商服务的实质。因此,“构建具有北京特色的营商环境指数体系”的内涵应该是在与世界营商环境标准接轨和服务型政府、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之下的“北京特色”。
09.
“首席数据官”在组织运营中的重要性似乎正在逐渐取代或超越“首席信息官”。《意见》提出,“试点首席数据官制度,全力打造一支懂业务、懂技术、懂管理的复合型数据资源管理队伍。”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市提出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以推进数据要素流动与赋能作用。但是是从具体实效来看,应该离首席数据官的职责要求与工作目标还有距离。在国家数据局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方案发布之后,“首席数据官”(尤其是相匹配的基层岗位)如何摆脱与数据资源报送、汇总、上下衔接相关的外界形象,如何从“+”的角色转化为“×”的效应,如果回看“互联网+”的推进过程,“数据要素×”的推进过程或将更为复杂,对行业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当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交易以及数商生态逐步发展走向成熟,“首席数据官”的职责与定位也将随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