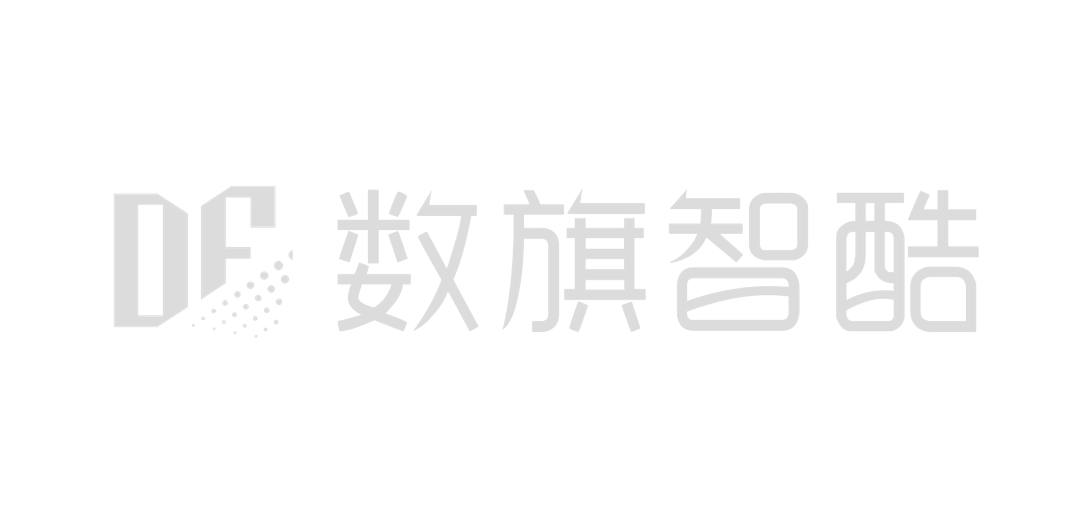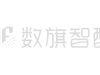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上海数字治理研究院与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联合发布了《2024城市数治向善报告》,针对“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价值判断与技术判断”提出了15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杜绝“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形象工程”的当下,以及大模型引发的GPU竞赛与知识恐慌让人无暇顾忌如何认识、评估和设置“善”与“恶”的禁区之时,提出“城市数治向善”不仅是对过去多年来的城市数字治理争论的一个注脚,同时也是面向多模态大模型可能引发的城市治理变革的一种期许与愿景。笔者有幸参与了报告前期头脑风暴的专家讨论,历时一年后再来看报告成果,又有一些新的思考和认识。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本·威尔逊在其著作《大城市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秩序是反城市的。混乱是城市的核心所在,但也正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吉尔德则在《知识与权力》中表示,高熵的信息的稳定传播与流动需要低熵的平台和通道。
那么,问题来了,当高熵的信息与数据进入“混乱”的城市治理场域,其结果就是超出人类想象力的突发与极端情况不断上演。而这其中,“作恶”只需要依靠不被驾驭的技术和无所收敛的人性的惯性,而“向善”则需要所有一切参与主体的努力。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城市数治向善”的反面并非“作恶”,而是城市数字治理在粗糙、潦草、鲁莽的罅隙里流露出来的“平庸之恶”——即每个人都恪尽职守、每个环节都遵纪守法、每个指标都符合考核要求,但每一个治理场景中的人及对象都无一不感到愤怒或者无奈。
“秩序是反城市的”,而数字技术介入城市治理的本质则是建立新的秩序——将权力内嵌于数据、平台与算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表象是以数字技术的“更快更高更强”来展现,底层逻辑则是依靠用数字技术放大了决策机制以及人性的善与恶。表面上数字技术更为高效直接地连接了城市与市民,实质上则间接地阻断和干扰了城市倾听到市民的真实心声。这种干扰不仅体现在数字平台的感知能力上,也体现在网络舆论对重大社会事件的“能见度”上。
“向善”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词汇,佛教讲“发心”,就是做事的初衷和出发点。数字治理的不同在于,即使当初的设计初心是好的,但城市数字治理场景是由设计者和使用者共同塑造的,在算法不断迭代过程中涌现出怎样的场景可能都是无法预料的。就像某市为了推广防诈小程序应用,结果为了完成任务就派人在地铁口附近随意拦下路人强行下载、注册和刷脸。
如果说“科技向善”是一个聚焦科技创新能力与应用伦理背后的责任担当问题,是一个更具有时间感的问题。那么“城市数治向善”则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遭遇与未来命运而与空间感有关的问题,这个空间包括城市的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城市数治向善”更是一个向掌握了城市发展命运与权力的决策机构提出明确的道德期许与权利诉求的问题。
城市数治向善,核心是在“秩序的反城市”与“数字化的‘再秩序’”之间找到平衡,以及建立以人的价值为依归的数治向善秩序。
人际之间的交往需要拿捏“分寸感”,数字技术与人的关系则是依靠像素与比特来定义,相比于无法言说的“分寸感”,像素与比特可以将数量和质量精确到一切可以或值得用数字表示的限度。城市对人口、资源、住房、交通等都有自身承受的极限值,而数治平台可能只需增加一行命令即可令城市随之进入一片混沌。对于一项治理目标而言,城市部门需要考虑各种关系、资源和考量,而如果失去对物理世界与社会运行的理解能力,数字技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标——数字技术所许下的城市治理乌托邦的所有承诺最终将以反乌托邦的方式进行兑现。
所以,城市数治的“尺度是否宜人”,我认为其关键是要将城市社会的暗知识、经验、常识等加入城市数治系统,以期建立数字治理的“分寸感”。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当我们认为必须学会像掌握自然力量一样掌握社会力量的时候,这不仅仅是通往极权主义之路,更是通往文明毁灭的道路。”如果我们回望一下城市数治的现实就可以看到,多少如梦似幻如数字乌托邦一般的城市数治场景不是寄希望于像掌握自然力量一样来掌握社会力量?
我们或许需要扪心自问的是:当我们希望利用数字技术对以“混乱”作为核心特征的城市秩序进行规范、标准以及“科学管理”的时候,其潜台词是否意味着我们试图利用自动化和机械化来迫使社会力量像自然力量一样可以被随意驱使、改造以及奴役?
因此,我认为“城市数治向善”首先要将无法被数据进行量化管理的城市规律与秩序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朴素日常,只有承认和接受这种日常,并调整决策的预期与管理的容忍度,抵抗一种依靠数字技术“人定胜天”、“毕其功于一役”的妄念,将城市看成一个具有正常“生老病死”的生命体,而不是试图利用数字技术去充当蛋白粉与玻尿酸永远让城市保持八块腹肌容光焕发,或许,“城市数治向善”才将真正获得发展的动力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