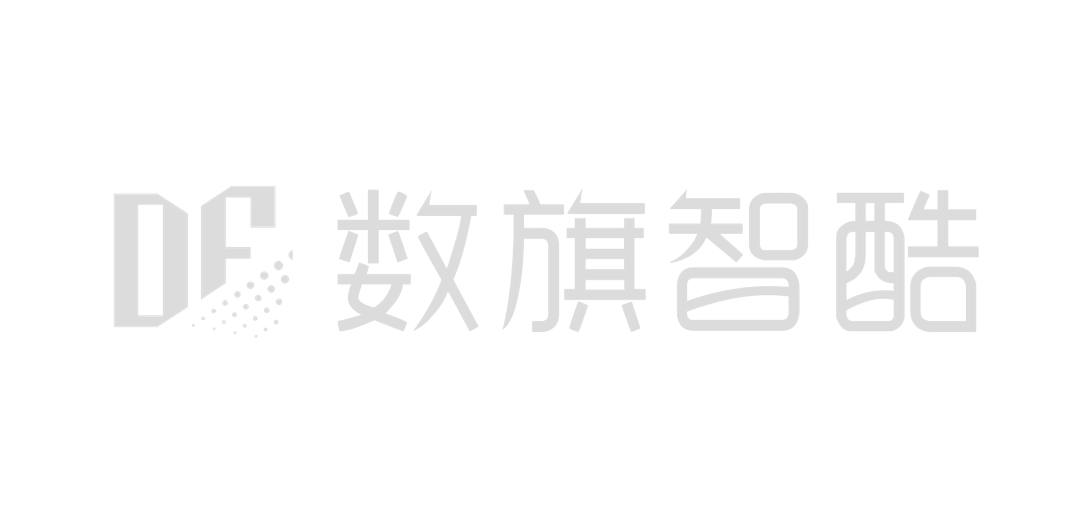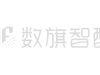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层层加码!部分基层干部花钱完成这一任务》),部分基层干部为完成相关数字化政务服务、线上学习等任务,只能花钱购买第三方服务,完成包括各类政务服务小程序用户注册量、账户活跃度、文章转评赞、学习时长等指标。
在考核压力下,通过第三方购买注册量、阅读量、转评赞等数据,“数字形式主义”成功地在平台经济的生态下找到了基层工作考核的“货币化”解决方案。而所谓的“数据思维”、“流量思维”终于在层层加码之下被平台反噬。
为政务服务平台(App、小程序等)“刷单”——一种消费主义与绩效主义结合的奇观。一般而言,商家“刷单”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或者在冷启动期间推动“数据飞轮”走向正循环。基层政府机构“刷单”并不对其治理和服务对象负责,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考核的需求。当形式主义得不到内部的自我纠正的时候,就会自动寻求外部力量来制造一种新的“形式”,以取代和消解前一种”形式“所造成的压力。“刷单”就是如此。于是,基层治理口碑与公共服务的社会效益被即时性地进行“零售”,通过淘宝的店小二以及小红书的博主们有求必应地“分布式”满足。
“政务淘宝”——像淘宝购物一样获取政务服务——曾经作为一种政务服务平台的用户体验方向出现。将“公民”设定为“消费者”、“顾客”,在技术繁荣的语境中从来没有人去质疑这种假设的合法性。而现在,我们看到了,当“顾客”而不是“公民”向平台提出需求的时候,当然需要受到上帝一般的对待,包括“刷单”和“买量”。当公共服务进入数字平台以不同形式进行供给的时候,我们似乎有意对“顾客”进行了过于浮华的修辞,而悄无声息地掩盖了公民的权利。
“政务淘宝”不仅传递了用户体验的便利性,也暗示了一种消费文化浸润的功利性。
淘宝、小红书的卖家与博主为政务App“刷单”,核心不是在出售一种所谓的“用户满意度”产品,而是在瓦解一种数字时代基层治理考核的根基,通过“数据麻醉”的方式斩断基层工作人员与公众互动的纽带。公众的声音与沟通的意愿被掩盖在巨大的流量、下载量和转发量之下,也就意味着数据本身成为了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最大的障碍与反叛者,而非一种积极的促进者。
“刷单”的本质是基层政府的群众信誉度被篡改、稀释后直接被批量外包给不具有任何群众基础与公共性的网络商家,他们像游戏一样荒谬地支配和遥控着一地基层政府的考核与排名。
对于政务App类似平台而言,流量、转发、点赞、下载量等数据包含了复杂的意义,指涉了公众的关切、基层的工作、背后的流程、任务的优先级等系列信息,而一旦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被釜底抽薪全部抽离掉,那就意味着一种“绩效通胀”,丧失了其本身应具有的价值。点赞和下载量是基层工作的一种抽象的显示。就像纸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有价值,其背后包含了等价的劳动时间、政府信任与社会关系。而一旦这个基础不存在,那纸币就只是纸了。
数字技术的应用让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发生了分离。新媒体平台的出现让基层治理的工作内容需要通过技术媒介来接受不可知的第三方来共同完成(用工作结果替换了工作过程),不仅考核现实世界里工作内容的完成度,还要考核数字空间里工作内容的能见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教授曾提出过著名的“行政发包制”,意指中国的绝大多数公共服务,包括一些属于溢出效应比较广泛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和社会保障、教育、环境治理等,都发包给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中央政府出资比例很低。现在,数字异化下的奇异景观出现了:基层政府为了缓解或摆脱数据考核的牢笼,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将考核结果外包给第三方来完成。所不同的是,“行政发包制”是将分包关系内嵌在上下级的权力关系中,而“刷单外包”是一种纯粹的交易关系。
基层治理相关的“刷单”现象能得到遏制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在《治村》一书中指出,乡村事务与熟人社会的复杂性,村干部处理村务需要的不只是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能力,更需要的是以灵活的身段在人情、关系、权威等交织的系统中以“非正式”方式来实现治理目标。所以,“严惩数据造假”或“打击刷单买量”可能并非我们需要讨论的重点,而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标准是否适应从土地革命跨越到数字革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