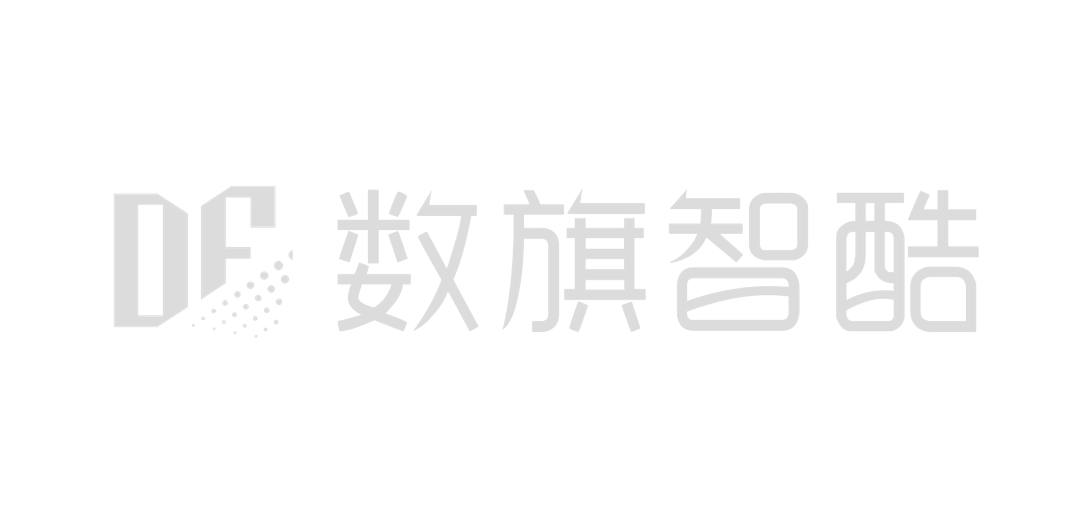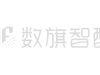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本文为《Uneven Innovation:The Work of Smart Cities》的书评

其实无需掩饰,全球智慧城市过去十五年的发展是“令人沮丧”的,这种沮丧不在于我们面对数字技术长驱直入的无力感,而在于我们自我催眠地沉浸于数字时代无远弗届的自豪感。
《Uneven Innovation:The Work of Smart Cities》(《不均衡创新:智慧城市的运作》)是2020年Jennifer Clark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其批判精神与反思气质,会不自觉地让我想起Shannon Mattern的《A city is not a computer》一书。二者之间的异同在于,她们都执着于对数字技术绑架的智慧城市叙事的批判,从城市的本质出发,反抗与抵制技术市场构建和渲染的智慧城市诸多不可能实现的“幻境”与“假设”。她们都认同,智慧城市的倡导者更感兴趣的是建造和实验新的项目,而不是系统而持续地解构和修复旧的生产方式与不平等模式。而差异在于,前者认为“城市不是消费者”,后者认为“城市不是计算机”。前者认为,智慧城市是一个经济问题与政策问题,而非一个技术问题,需要公共部门获得更多定义和塑造智慧城市的主动权;后者认为,要解决智慧城市的技术沙文主义倾向,需通过社会化协作将本地知识、文化、历史等(比如建造图书馆)嵌入解决方案,以创造智慧城市更多的丰富性。
近十五年以来,“Smart”与“Wisdom”的争论(智能城市或智慧城市)似乎是横亘在中西之间的智慧城市“重大意识形态问题”,“Smart”主义者嘲笑“Wisdom”的虚无与不接地气,“Wisdom”主义者看不上“Smart”的浅薄与没有内涵。但是,这种争论的共同结果是,让智慧城市的“智慧”被阐释成为一种东方式的、聊胜于无的、无法走出书斋或研究报告中的“学术正气”,并未为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带来任何值得褒奖的成绩。也就是说,对技术的默许和纵容让作为城市发展多样性的规划与建设理想没有剩下多少可以实践的空间。城市公共部门、投资机构、技术厂商急功近利的建设方式,让管理者、建设者和市民都没有时间去等待、验证和收获一个理想中的智慧城市。
而如今,我们沉溺于一切基于智能手机、二维码、短视频、直播间、智能驾驶、机器人等智能应用,我们自以为得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智能时代的自由。我们将“便利交换自由”等同于“便利就是自由”。这一切都有被数字资本主义主导的智慧城市传播思潮有关。“智慧城市是复杂巨系统”的表述,更像一种掩盖自我无能的宏大叙事修辞。而“新型智慧城市”则更像一种话语修复策略,在承继过往、不否定从前的基础上,对技术至上主义者的热情与吃相进行敲打与纠偏,但在数字经济、平台竞争、政策取向、技术“反身性”等不断作用的现实下,也无力实现一厢情愿的蓝图。最后只有略显讽刺地在所谓的“评估结果”上给予一种“自证清白”的数据化论证。
Jennifer Clark提出,“智慧城市不是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经济问题的新表现。智慧城市项目的道路是从不均衡发展到不均衡创新”。在作者眼中,那些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智慧城市概念与叙事,其内在核心都是被城市政府和技术厂商由于利益驱动所竭力掩盖的经济事实:一部分人的极端便利或超额回报必然以另一部分的权利受损作为代价。就像网络外卖的低价和迅速是以外卖骑手的辛苦与伤亡作为代价,而网上拼单购物的极致体验则是以批发商的生不如死为代价。所谓“共赢”——这种诞生于工业时代的谈判哲学,或是一个妥妥的、只能从相对意义上理解而无法从本质上实现共情的商业话术。作者认为,城市政府与公共政策部门只有勇于承担责任,去打破那些梦幻叙事的假象,不断调整整个城市社会的利益平衡,才是智慧城市逐渐趋近于平等的正确发展路线。
01.“模糊性”:智慧城市原罪的滥觞
如果一个词语在意义的丰富性、边界的不确定性以及利益上的包容性均具有无尽的想象空间,既有所向披靡的进攻性,又有无懈可击的防守性,这在东方文化语境中通常被视为“智慧”的表现。“智慧城市”正是这样的词汇,具有一种令人爱不释手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的本质通常潜藏着不同利益主体心照不宣的契约,而实质则指向一种获得各方认同但谁也不承担具体责任的政治正确。既然无法达成共识,那就模糊它的概念与定义,然后替换和篡改它的原意。这或许是过去这么些年我们对“智慧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观念的处置方式。
智慧城市在定义上的模糊性与灵活性,被视为具有可以进行话语操纵和叙事建构的更大空间。那么,智慧城市是如何利用这种“模糊性”来清除发展障碍的呢?首先,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叙事,无论是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还是项目创新,现有的城市研究理论都无法立刻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反叙事”——以驳斥智慧城市建设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其次,智慧城市在不断阐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城市本身并行不悖的平行叙事,让人产生“智慧城市建设不会破坏城市社会而是升级城市环境”的错觉。而现实告诉我们,数字技术介入城市运行的生物性所带来的不只是治理和服务能力上的高低,还涉及权利、伦理和价值观上的渗透与转型。
那么,智慧城市的“模糊性”是如何对不同的城市主体产生影响的呢?
学术界的诸多批评认为,“智慧”一词掩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居住在城市的人们以及城市运作系统的有限理解。“智慧”不指向责任、职能、行业、领域、区域、身份等任何具体的标识对象,它指向一个让人无法准确把握却又极度向往的整体——城市,这使得城市政府、企业和市民的诸多寄托都处于“悬浮”状态——与城市有关,但不确定具体由城市的哪个部分实现。
作者认为,智慧城市项目破坏的不仅仅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界限,还进一步侵蚀了心理契约。智慧城市行业还质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以及不同角色带来的权利和责任。公民和居民的权利和责任同样模糊,而且越来越不稳定。如何理解这种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呢?伴随智慧城市崛起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让以Uber、Airbnb、美团、滴滴等为代表的平台公司,它们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在城市的道路、社区、电梯等频繁“圈地”,围绕它们衍生的城市社会冲突越来越频繁。然后它们为了提升利润而抛弃传统的雇佣关系就像抛弃一种不受资本市场待见的历史累赘,并巧妙地利用了平台与数据的强势地位,从而构建一种平台、劳动者与社会之间的奇异关系——平台外包了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企业责任,并通过“平台—用户”之间的发包模式塑造了以“灵活就业”为名的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者。
因此,作者在书中指出,智慧城市项目建立在并延伸了新自由主义的标志性趋势:私有化、分权和放松管制。它允许智慧城市中进行的工作在传统雇佣关系和传统工作空间之外进行。正如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再生产的负担已经从公司转移到国家和个人一样,提供工作平台的负担也转移到城市和工人身上。传统的雇佣关系被解构,所谓“家的温暖”、“组织的关怀”都与平台劳动者无关,每个人都寄居于系统里,像游魂一样出没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当他们遭遇不幸或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唯一的机会就是独自向政府和社会求助——机场和车站的网约车专用通道、疫情期间的上海和深圳外卖骑手休息补给点,这些都是平台的用工成本被抛向社会进行公共分摊的例证。如果以共享单车为例,我们会发现其生动地验证了“不均衡创新”对城市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与知识经济的创新服务的风险收益被企业和创始人所捕获,而一旦出现项目失败则由政府部门来收尾。所谓的“共享单车坟场”就像一道伤疤被永恒地刻在城市的身体上。
模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将“消费者即生产者”视为一种平台经济才有的“用户福利”与“在线荣誉”,其实质来源于数字平台的结构性偏差,这也是智慧城市依赖的另一种话术。Uber的乘客与司机同是平台的消费者,他们依靠平台提供乘坐服务、路线导航等相关服务,但同时他们也是平台的生产者,为平台提供道路拥堵、交通事故等数据。值得玩味的是,当智慧城市行业在鼓吹“消费者”权利的时候,它们似乎选择性地遗忘了“生产者”的收益——Uber司机是否应该获得作为数据生产者的相关劳动收益?(这一点曾经引发了Uber司机的抗议)
更值得深思的是“共建共治共享”,这一理念近乎完美地概括了一种具有未来感的城市发展方向,但也极大地动摇了市民的权利与责任根基。“共建”是作为城市建设者的责任,“共治”是作为城市治理者的法律框架内的履职行为,“共享”则是作为被服务的消费者的权利,将三种不同属性的城市角色合为一体,然后赋予一种超越了城市运行常识的愿景,这或许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责任、义务和权利的混搭,也越来越多地激发了城市基层的微观冲突。
智慧城市项目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的贡献“模糊性”。大凡所有的智慧城市项目都具有经济性使命,且在发展后期我们会发现,智慧城市项目的起源是作为数字经济招商引资的“政策性回报”来实现的。因此,智慧城市建设究竟或如何对地方经济产生作用,这其实已经取决于引入企业发展的稳定性以及城市政府的周期性工作重心。最后变成:我们都知道智慧城市对经济发展有益,但不知道具体对哪些方面有益。
作者认为,智慧城市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性与创新性的发展模式,依靠官僚系统的常规性理性选择,往往会造成一种无意识偏见,从而错过真正改变城市的机会。或者说,智慧城市建设是以城市市民为目标,而推进模式却是多维度和跨国家的。建立在梅特卡夫定律之上的智慧城市理念最终需要通过自愿网络来推动,而依托行政等级制度推动的智慧城市在建设之初其实就已扭曲了其未来发展基因。
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当倡导“城市即平台”的时候,我们被提醒要警惕平台资本主义的“侵略性”,要将利益愿景托付给代表公共利益化身的政府;当呼吁“政府主导”的时候,我们又被告诫要警惕官僚系统的弊病,要推动“市场参与”的平台运营商来提升体验以及构建扁平化的协作机制……这种自说自话、左右互搏的矛盾,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俯拾皆是。
或许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让作者认为,将智慧城市的价值讨论从城市转向更模糊、更分散、更不确定的地域,其实就是对经济问题的政治性回应。这或许就是我们作为“政治人”的条件反射: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将这个问题提升一个解决等级。更宏大的问题往往用来匹配更无解的现实。正是在定义城市问题范围上的“模糊性”,为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潜在解决方案打开了大门。就像发热可以服用退烧药、感冒可以服用感冒药、胃痛可以服用胃药,而当你口干舌燥精神萎靡肚子还不舒服的时候,所有人都告诉你:多喝热水。由于城市问题的“模糊性”存在,被数字技术厂商在会议室里精心推敲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热水”。
02.“场景”的魅惑:智慧城市建设与“制造不平等”
作者认为,城市问题不是由城市的特性产生的,而是由经济的特性产生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大城市病”则意味着需要另一种审视视角,城市问题的出现并不在于肉眼可见的体量“大”,而是其经济特征、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医疗、交通、教育等系列问题。以北京为例,“疏导非首都功能”的本质是转换首都经济结构。
当平台经济公司带着“云资本”进入智慧城市领域的时候,“场景”开始作为一个性感的词汇频繁出没于PPT、研究报告、工作方案等地方。为什么“场景”突然如此受到欢迎?作为一个有别于系统、平台、应用、工具、功能等的词汇,既脱离了“纯技术”导向的“低级趣味”,又符合城市政策设计与执行者的审美。“场景”的流行,不仅让技术厂商排除了“技术与业务两张皮”的质疑,同时又让城市政府拥有了“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尊重。
当“场景”成为一种多方认可的合作话语时,“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开放清单”似乎就成为了数字时代推进城市民主化实践的新尝试,这不仅符合“多维度、跨地域”的智慧城市精神,同时也符合政府与市场合作的发展要求。只是这种城市民主化实践最终是以一种予取予求的市场化机制来实现:城市承诺开放场景让企业产品落地,企业承诺对城市进行数字化投资。
智慧城市场景的本质是一个针对时间、空间、对象、边界、权力、流程等要素的制度化封装,场景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手段,一个场景就意味着一个问题。
“场景”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在于,当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场景”则是一个局部,“场景”与城市是一个动态的相互调试过程。也就是说,当某个“场景”应用付诸实践的时候,城市在不断变化中可能滋生出新的问题,甚至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而从智慧城市建设实况来看,无数的场景最终被外包给无数个不同的大小公司,它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案,代表不同的部门利益,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当它们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场景”植入到智慧城市的身体的时候,发生痉挛与生理紊乱几乎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如果有人觉得所谓的“数据底座”、“城市操作系统”可以解决不同场景的连通性与互操作性问题,那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饱含技术信仰的天真与肤浅。
讨论智慧城市的“场景”,就必须讨论为什么业务云化、去地域化的科技公司会突然对城市感兴趣?以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特斯拉等为代表的大型科技公司,它们正在被成为收取“云地租”、瓦解资本主义的“数字封建主义”势力,在长期的数字乌托邦主义推动下,数字科技公司似乎被形容为只存活在数字空间而与人间烟火无关的独特存在。但是智慧城市崛起的另一个背景似乎告诉我们:数字的物质性正在凸显。这种“物质性”并不是指数字和代码必须显示在一台由金属、塑料和芯片制造与呈现的显示器屏幕上。而是数字科技公司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权力正在进行短兵相接。Amazon为了避税就可以宁愿关闭设置在某地城市的仓库也不愿改为子公司,Google在一个偏僻的州以建设云计算中心的名义低价买入一块地进行囤积等待升值或挪作他用,丰田就选择在富士山下的750英亩地将氢能源、自动驾驶以及“数字公民”纳入到这个微型智慧城市的“实验玻璃瓶”,Uber为了推进在城市内部的业务就专门在平台设置一个“灰球”系统将与它作对的官员拉入数据库让他们永远无法叫到车。
作者认为,科技公司的地理位置从来都不是生产地点,而是关于其市场的地理要求。或者这样我们更可以理解,为什么Apple和Tesla要将数据中心设立在中国,而中国的门户网站都要将新闻中心设置在北京。此外,城市不仅是购买智能城市系统和平台的对象,并且还需为市民提供服务和基础设施。城市是各种产品和服务补贴和降低风险的场所,这些产品和服务远远超出专为智慧城市应用设计的范围。城市既是生产地点,也是消费地点,还是确定、设计和原型新产品、新系统和新平台的地方。因此,城市是整个生产过程(从创新到生产再到消费)的战略选址地点。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与其认为深圳、杭州是由腾讯、阿里巴巴等数字科技公司及其生态所助力崛起的新锐城市,不如认为深圳与杭州无论在政府补贴、就业环境、财政慷慨度以及对数字技术的宽容度都具有不可阻挡的吸引力,更适合新兴科技公司的生存。无所谓谁成就谁,它们只是各取所需。
作者对“不均衡创新”的第一个解释是:“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地理学的标志。这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未能均衡发展,而是由于偶然和随机因素,资本主义的地域发展代表了从总体均匀过程中的一些随机偏差。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统计性的”。在此基础之上,智慧城市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节点或插曲,它既弥漫着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利润等令人向往的核心要素,同时也充斥着不容回避的功利、紊乱以及崩溃。所以,我们也应该将智慧城市推进过程中产生的根本不平等理解为一个特征,而不是在经济操作系统中产生和再现这些不平等的一个“错误”。就像我们应该将“AI幻觉”理解为大模型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Bug一样。
作者提出,城市不负责制造“不平等”,而是提供舞台让“不平等”在其中上演。这种“不平等”既是横亘在科技公司与其他传统企业之间的政策、税收、补贴等的不平等,也是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贫困”人群、“数字鸿沟”导致的弱势群体等产生的社会保障、福利以及城市权利的不平等。智慧城市项目本质上不是为了提供平等的机会来管理市场失灵,智慧城市本身就是市场失灵的一部分。
作者的第二个解释可能会打破了我们以往对智慧城市的某种迷信:“智慧城市是一个由行业驱动而不是由公众驱动的项目。因此,智慧城市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创造消费者,而不是为公民服务”。作为一个由市场利益主体来推动的项目,为了创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与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有些智慧城市项目会蠢招百出,有的智慧城市场景会饮鸩止渴,因为最大限度地攫取市场和消费者身上的利润才是符合其本意,所谓“为公民服务”则只是政府和市民一方的私人化期待和文学化想象。不仅如此,在数字鸿沟、数字消费差异方面,智慧城市项目会自动去适配和调节,以所谓“定制化”、“个性化”供给的模式来利用这些差异,而不是减少差异。而这也使城市社会在数字时代的环境中裂痕越来越深。作者表示,“智慧城市行业旨在制造和服务不同的市场,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产品和服务付费”。换句话说,智慧城市项目没有所谓的“公共性”,它有来自市场基因附带的商业使命。
作者针对“不均衡创新”的第三个论点认为:“智慧城市行业正在推动城市和公民开展新的城市创业形式”。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不难发现,以前是通过落地产业园、创新中心以及创客基地的方式,实现城市与科技公司的技术生态合作,现在是通过AI数据训练基地、自动驾驶路线、低空经济试飞区域等争夺新一轮科技企业。由于科技公司的经济表现与技术辐射效应,无形之中在城市之间造成了一种紧张的竞争性氛围。为了在数字经济的竞争中拔得头筹,科技公司以“总部”、“**区域总部”、“**第一城”等相许,各个城市你追我赶地加速推出政策、试点等,从而让城市政府已没有时间、精力和充分准备去研究政策的风险。
或者说,科技公司首先用平台的数字消费重置城市的生活空间,然后又用在线会议、直播视频、O2O应用等重置了城市的工作空间,现在它们开始通过以海量用户的数字应用打造所谓的“城市服务入口”来重置城市的治理空间。
我们不应该指望智慧城市具有“内在的进步导向”,如果我们不是下意识地去对智慧城市项目的公平性做刻意的设计,那么它的结果与以往任何城市项目的结果无异。这是作者对智慧城市决策者、建设者与市民的告诫。所不同的是,智慧城市项目对城市社会和物理空间实实在在产生干预和影响但又无需经过像其他城市项目的审批和问责程序。这一切都归功于智慧城市厂商对项目愿景、理念、价值、意义的憧憬能力,让甲方置身于一个扭曲立场忘记了自身在做一个可能影响成百上千万人具体的生活的决策,而只是在做一种随时可撤销的可能性尝试。
03.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掩盖问题
在数字时代为城市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是一件既有挑战性又有满足感的事情。因为大家的潜意识均认为可以向数字技术求助,只是解决程度的高低而已。对于科技公司而言,“技术为城市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唯一的问题是选择哪种解决方案”。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它们在招标的企业选项中其实就已经框定了可选的对象,它们掩盖了选择的可能性,并将替代方案也限制在自身的容忍范围内。由此,最终被选中的是各方利益达到平衡的方案,而不是真正匹配城市问题的方案。
对于智慧城市而言,如何识别问题,由谁来识别问题,谁掌握了定义城市问题的权力,什么力量和利益在驱动城市政府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政治。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则是在这些问题和利益得到确定与博弈平衡时候的结果。作者提醒道,智能城市项目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其背后的引人入胜的叙述。智能城市绕过了城市政策和城市问题的历史和复杂性,并将关于城市的对话重新设置为从技术解决方案开始,而不是问题识别。
作者认为,必须更好地理解城市,而不是技术,才能追求智慧城市项目的潜力。如果从一些成熟的智慧城市应用案例来看,预测性警务、智能交通系统、雨水管道监测等都曾被视为智慧城市的创新能力象征,但是这些都是观察城市问题的数字化方法,并不是解决方案。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城市的某些特征,而在于经济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数字技术只是在缓解和调整因为经济特性带来的城市压力,但并不会完全祛除这种压力。
智慧城市本质上是一种新的“造市”运动。城市既是智能城市对象、系统、平台和数据的制度性客户,也是定义和界定面向个人、机构和其他公司的智能城市产品和服务消费者的地理容器。城市既是市场的消费者,同时又是市场的创造者与管理者。
在城市行政版图的管理上,城市是强势权力者,而在智慧城市的博弈天平上,城市又是权力弱势方。数字技术的全方位介入,让城市逐渐失掉了对传统、历史、文化、知识、权威等的确定性敬畏,处于一种对未来没有把握、对过去没有留恋的尴尬状态。
所以作者表示,智慧城市的对话是关于城市规划和政策的对话。它需要将城市的职能、运作、历史、文化、系统、政治和地理等城市专业知识,与数字技术、城市空间、城市社会现实、城市政策等新兴知识相结合。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共识,我们所谓的创新模式很可能是一种陈旧、过时、不得人心的选择。
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宗旨,其实已在不同的场合出现明显的分裂。作者认为,诸多城市政府所关心的依然是智慧城市能否为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提供官僚化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为市民增强和提升市民的访问、机会和参与能力。当然,还有的城市政府希望利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来建设智慧城市项目,试图从小微项目的冷启动开始发展成为庞大的系统规模,这种建设思路曾一度被广泛认同,但其致命的缺陷在于:智慧城市项目(场景)都被设计为一批解决具体问题的离散化解决方案,根本不具备为城市系统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智慧城市的框架内,希望通过数字赋能来推动城市实现所谓的“整体性转变”、“革命性重塑”,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缺乏逻辑基础的奢求。
作者指出,希望用技术解决方案解决城市问题的言论不仅有点幼稚,它还否认了真正的问题和对真正解决方案的需求。那么,究竟何谓真正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我想它肯定不是技术厂商在PPT上美轮美奂的数据和视觉界面,而应是整合了问题识别、政策设计、市民参与、技术实现、效果评估等一整套要素的城市问题解决过程。
04.智慧城市是“单数”,而城市是“复数”
很难描绘哪一种“城市”才是我们当下的选择,玻璃幕墙与高楼林立是城市,田园诗般的园区草坪也是城市,曲折幽深布满创意的阡陌巷落是城市,层峦叠嶂的立交桥也是城市,贫民窟城中村是城市,纸醉金迷也是城市……这些“城市”意像的存在让我们很难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是否是“城市”有准确中肯的判断。而智慧城市似乎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用最流行的技术搭配最时髦的slogan,城市技术服务商告诉我们:看,这就是智慧城市!
本质上而言,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或场景是“单数”,而城市是“复数”。而对于“城市”这个词本身,它的单数形式具有误导性。城市是由不同主体、空间、环境、利益等构成了多种混合的存在形式。所以作者表示,“城市是地理和社会上不平等地分配收益和损失、特定经济体系中的赢家和输家的不平等的空间化”。“城市不是城市问题的起因,而是城市问题的场所”。城市问题并不是由城市本身造成的,而是由生产组织本身造成的。部分城市的独居老人老龄化问题,其存在更多是由当地的经济发展、教育现状、医疗设施、社区服务等造成的。独居老人应该被视为城市经济的一种阶段与状态,而非问题。
从这一点而言,我觉得《大城市的兴衰》一书指出的“秩序是反城市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城市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时空存在,而没有制造某种问题的动机,城市本身既不是混乱的制造者,也不是秩序的守护者,在混乱中找到短暂的秩序感或是“复杂”与“规模”作用下的城市真谛。这也应是“城市即平台”的真义,这个“平台”不再被数字科技公司所独享,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活动、意义、技术等创新不断上演的平台。
曾经有一种讨巧的论调认为:智慧城市不仅需要智慧的市民,还需要智慧的市长。在领导哲学、现代管理理念的感染下,大家似乎都一致认为,有一个智慧的市长就能更有把握地建设智慧城市。那么,那些大城市的市长似乎每天都面临着来自城市问题的拷问,或者是交通事故,或者是失火事件。作者认为,大城市的市长其实承担了工业体系紧张、不适、失调和失败的责任,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无辜的。这或许就像一个市值千亿美金以上的公司CEO,事实上很多来自董事会的决定、基层员工的问题以及公司政治都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他看似掌控了整个公司,其实只是一种宏观的政治上的控制,而非一种微观的治理上的驾驭。
智慧城市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市场问题,而不是治理的失败,它遵循经济发展特征与产业链分布,而不是管辖范围。而智慧城市项目已经成为一个非历史、非政治和去领土化的话语,这些地方是由其地理、管辖权和治理以及历史定义的。这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一对悖论。如果以中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家电商平台可以将总部设在北京,客服设在西部,仓库设在长三角,而快递员遍布全国。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一个网约车公司准备在某城市运行的时候,它的注册司机因为没有本地户籍而被打击为“黑车”禁止营运;当某电商公司从自建仓库配备大量货源和快递员准备进入一座禁足的城市的时候,它们因为疫情管控被拦截在高速路口……所以,当讨论“智慧城市是一个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许还需要讨论这是一个“市场经济问题”还是“管制经济问题”。
此外,作者认为还需要关注智慧城市的规模问题。当城市问题的过于宏大,偏向于解决可识别的具体问题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是无能无力的,然后它们被冠以看似前卫、先锋的名字,却干着沿袭了过去多年来一直秉持的城市工程建设模式。
当然,数字化、网络化视野下的城市问题解决思路越来越新颖,比如“众包”、“黑客马拉松”以及“数据创新大赛”等,但这些真的是我们要寻找的破解城市问题的终极法则么?作者认为,“这种以黑客马拉松为灵感的城市服务方法,其结果是在缺乏目的性和互操作性的平台上建立的一层又一层不相关的努力”。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意思就是一大群有创意有能力的人做了一件标榜了自我但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些通过所谓“众创”完成的每个项目可能都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和优雅设计”,但是它们可能缺乏对整个城市系统具有持续性研究和独特性认识。最终,所谓的智慧城市创新方案成了每个团队自己创造的“人工制品”。而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需要一个观照当下、回望历史、并守望未来的“有机物”。
05.智慧城市:一场私有化与公有化之间的争夺战
20 世纪 90 年代,《资本的限度》的作者、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曾经提出:城市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的特定场所。而现在,从工业时代过渡到数字时代,城市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巨头积累“云资本”或“数据资本”的特定场所。无论是类似于谷歌这样的全球性平台经济公司,还是像其旗下的Sidewalk这样的本地化智慧城市公司,它们要么通过数字应用、智能设备、城市服务等收集城市用户和行为数据,要么希望通过部署在城市的传感设施大规模采集数据,当然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让城市更智慧”。
于是,第一个问题出现了:私有化运营vs公有化供给,智慧城市项目以及公司采集的数据属于谁?
数据既是智慧城市的终端产品,也是智慧城市的输入。因此,作者指出,“数据私有化就是整个智慧城市项目的私有化”。智慧城市的批判核心,不是一个“智慧城市为了谁”的问题,而是“谁拥有智慧城市”的问题。谁拥有并运营部署在城市中的智慧城市产品、系统和平台,并有权从其中提取数据?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的逐步私有化,正在为地方政府收集和处理公民和居民的特性和行为数据的商业用途奠定了基础。如果对照某市政府将公共数据打包售卖的新闻,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它们已经在潜意识里将公共数据视为一种可由市场需求支配的商品。
在智慧城市高速发展的现实下,数据的交易和使用受到监管,但没有人质疑收集这些数据的公司拥有这些数据的权利。也就说,我们的热情在于对“数据黑市”进行合规监管。作者担心的是,由于智慧城市公司的商业化策略,使得开发智慧城市市场的指导假设是,“将公民数据货币化可以遵循与在技术行业测试的公司战略相同的做法和标准,将客户数据货币化”。它们对数据处置的路径依赖就将公共数据货币化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然后回头再论证其正当性。这样的闹剧其实在城市智慧化过程中频频上演。
作者毫不避讳地指出,事实上,数字技术厂商已经将所提供公共服务相关的诸多数据存储于城市之外,除非有合同安排明确规定了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方式,或者对信息的使用有监管限制,否则私营分包商就有机会将公民数据商品化,而无需征得同意。如果回看国内,为了推动城市数据的共享与应用,我们提出了“一场景一授权” 、“数据可用不可见”、“原始数据不出域”等诸多看上去令人神往的数据流通应用模式,但是核心都是为了解决数据的安全问题,而不是数据的所有权问题。而现实是,除了过度地强调安全、安全和安全,城市政府尚缺乏对数据所有权如何治理和支配的完整认识。
智慧城市公司或平台究竟生产或付出了什么?事实上,智能城市公司并不为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支付两种基本投入:基础信息或系统平台内的用户数据。也就是说,它们所声称的能力与智慧的根基是城市的基础信息以及城市运行的业务数据,而这两种数据被它们免费征用而不需要支付任何投入。这种权力的不对称性,使智慧城市平台无偿获得了城市基础信息以及相关业务数据,但却对用户拥有巨大的控制权。
第二个问题是:公民的角色与消费者的权利如何在智慧城市进程中进行权利安排?
以智能汽车为例,当信息系统与通信技术将汽车从个人驾驶员的手中解放出来,汽车实质上在完成从离散的制造对象到嵌入服务的商品的渐进式转变。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将颠覆现有厂商的收入来源、保险模式、债务融资以及后汽车市场。比如它将通过汽车驾驶行为数据来决定保险费用,而后汽车思维将不是维修发动机或包养轴承,而是定期升级数字系统与AI能力。而重要的还不是汽车自身的自动化水平,而是部署自动驾驶道路的环境——车道线的清晰度,汽车传输数据的速度,行使环境中其他行为者的动向。而这些都是需要城市政府、交管部门以及其他市民进行支持和补贴的。城市不仅提供街道,还提供了街道的地图和标志,未来可能还要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数字化道路的感应系统。这就是在智慧城市中自动驾驶汽车对公共道路资源进行私有化的过程。
自动驾驶汽车的例子表明,在智慧城市实施中,公民的角色和消费者的功能之间的概念和操作差异需要澄清。智慧城市数据是由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动态参与者生成、收集、存储、聚合、分析和使用的(包括出售)。这一现实使在实施智慧城市战略时建立开放数据框架变得复杂。当私营公司(而不是城市)提供产生和收集信息的公共服务时,并不完全清楚什么是公共数据。而当它们对数据有处置需求的时候,则会路径依赖地进行货币化处置。
这也暴露出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智慧城市的服务设计和交付不是一个公共项目,而是一个公私混合空间,并且公私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不稳定的且随时发生变动的。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智慧城市项目不仅是在提供服务的物理景观不均匀的情况下展开的,也是在谁提供特定服务的组织景观不均匀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获取一项城市服务的时候,我们其实无法准确区分这项服务是由城市政府提供的还是平台厂商提供的,因为从数据、设计、接口、体验、运营等均已分属不同的责任主体。
智慧城市还需面临的一种挑战在于,在城市的行政权力边界和公司的商业权力边界之间,市民的权利应被如何看待?一个常见的案例就是,当微信和支付宝的用户数据都达到10亿级用户规模的时候,一座与微信合作推出数字公共服务的城市拒绝了支付宝的合作,或一座与支付宝合作推出数字公共服务的城市拒绝了微信的合作,需要问的是,对于城市当局而言,谁可以做出这样的决策?是否需要征询市民的同意?当公司的商业权力影响大于城市的行政权力影响时,处于谈判弱势的城市当局如何保护市民的利益,以及公共服务的稳定性?比如合作平台的服务突然宕机、下线或中止合作。
智慧城市建设中产生的“不均衡创新”促进了从数字鸿沟向数字包容的转变,这让我们又一次见识了修辞的力量。“数字鸿沟”的潜在含义是政府的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造成区域的不均衡。而“数字包容”就意味着城市和社会需要负起帮助数字弱势群体去适应数字化进程的责任。它们隐含的共同假设是:在智慧城市项目过程中获取了丰厚利润的企业是没有责任的。
科技公司为目标消费者设计产品和服务,而城市需要为所有市民提供服务。公司可以停止生产,但城市继续管理和服务。城市需要持续性,而数字服务可以随时宕机。城市的建立是为了提供这种不间断的持续性。为什么智慧城市越发展,我们需要安装和下载的App越来越多?数字形式主义越来越猖獗不可遏制?因为智慧城市项目往往过度地关注用户群体与功能的“定制化”与“适用性”,最终导致城市的连续性与持续性均被割裂,市民和管理者的时间流逝在一个个数字应用的关闭和重启中。将“技术解决方案”等同于“公共服务”或“治理工具”,这是智慧城市厂商巧妙而精致的偷梁换柱。
如果我们到媒体报道里去看一看,会发现公众、企业和政府似乎都对智慧城市感到“兴奋”,只是他们的兴奋点各不相同。公众对智慧城市的兴奋是“由关于颠覆性技术将如何改变建筑环境的说法所驱动的”。数字平台企业对智慧城市的兴奋在于通过平台的辐射力与掌控力可以实现对城市公共设施的私有化,并营造一种“在线社会主义”的幻象,享有“城市新型基础设施”的美名。政府对智慧城市的兴奋在于以有别于以往任何城市项目的弹性可控的方式来推动智慧城市,在数据与算法的辅佐下获得对城市淋漓尽致的秩序感与掌控感。
过去这些年,将智慧城市的战略目光从国家、城市群、城市、城区,进而下沉到社区,我想这不只是考虑市民“获得感”的结果,而是在政府、企业、平台等均意识到智慧城市的项目、系统以及场景只适合在有限空间解决具体问题。对于一个空间、人口、产业过于庞大和复杂的不均衡的城市而言,智慧城市项目的绩效显得过于虚无缥缈。而在一个可控的几平方公里的社区,作为一种技术扩散模式的智慧城市项目可以如鱼得水、有声有色地在各种不同的聚集区运作和产生创新。这或许也是全球城市都开始着眼于社区、实验室、基地、特区等建设的原因。而对于这一点作者似乎并不完全赞同,我想她想要表达的核心要义应该是:智慧城市项目的“城市”不仅应包括它的“所指”,还应包括它的“能指”,而城市中的“人”则应是更广义的“市民”——不只是有户口或有住房的那部分人。
越来越多的智慧城市项目默认为计算机做出决策的平台,而城市政策是基于人们做出选择的概念。个人选择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
我认为,这包含了作者对智慧城市发展的复杂感情——当崇尚数据理性的机器决策被用来管理非理性的人类行为,这本身就是无解的问题。
结 语
在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之下,智慧城市领域其实在进行一场“猫鼠游戏”——城市政府想尽千方百计希望搞清楚技术的内幕和对业务的影响,技术厂商则费尽心机在解决方案的措辞与表达上将技术描述故意复杂化。长此以往,智慧城市的技术服务部门不仅学会了如何掩盖自己的真实动机,还会越来越掩盖自身在其他领域的运作。
只有停止通过技术解决方案继续复制不均衡的发展模式,才能将智慧城市从技术叙事中解放出来。另外,不要相信智慧城市的“精彩案例”,因为这类案例的本质是对技术能力的炫耀式表演,而不是在城市和区域发展变化在长周期内的真实反映。因此,智慧城市专家除了了解技术之外,还需要了解效率、公平、分配和影响。
十年前,移动互联网的崛起让中国智慧城市走向高歌猛进的发展期,基于新媒体应用的移动政务服务供给空前繁荣与强大,我曾提出公共机构可适当向平台让渡部分权力,让它们利用平台的溢出效应更高效地承担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责任,以及改善公共部门的协作质量。十年后,我发觉这是一种憧憬技术乌托邦的幼稚病,就如作者所言,公共机构面对无节制的技术输入,应该主动去塑造智慧城市的未来,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数字技术。(完)
注:本文还得到了波兰格但斯克工业大学教授Tomasz Janowski先生关于《Understanding The Failure Of Smart Cities:Smartness VS. Sustainability VS. Continuity Tensions》演讲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