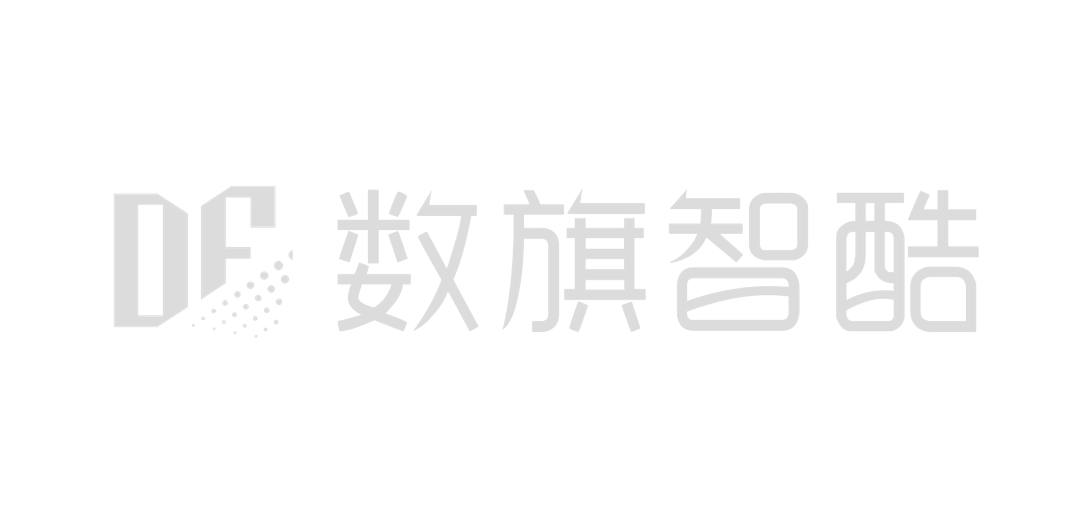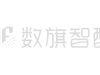事情缘起于四个郑州高校女生晚课后想去开封吃灌汤包,于是结伴夜骑,这一举动在社交媒体得到了其他同学的响应。当骑行开封达到一千人左右时,开封官方发出了景区对夜骑大学生“免门票”的通知,夜骑人数开始呈几何倍数上升,最终达到近20万人次,随后开封城区严重超负荷运转,从郑开大道驶来的共享单车呈“围城”之势,饭店、旅社、景区全部无法接待,郑州至开封的骑行路严重堵塞,正常的城市运行秩序已经被打乱。郑州官方开始宣布交通管制,哈罗、美团和青桔三大单车平台联合公告,超区将强制锁车。
○ ○ ○
“开封夜骑”如果是一个城市营销方案,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这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营销方案;如果将它看作是一个跨市域的城市治理场景,那么则是一次对数字治理“叶公好龙”的“高效”实践。
“开封夜骑”再一次证明了《大城市的兴衰》一书中提出的“秩序是反城市的”这一观点。而在混沌与未知中不断探索和抵达城市的本质以及市民的内心,则是每个城市治理参与者的智慧所在。
诚然,当城市运行状态走向失控,果断阻断形势发展是有关大局的决策,但是,当城市的“反秩序”现象层出不穷,如果我们认为只需要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任何不可控的城市问题,那城市就会“没有任何问题”,与此同时,“人民城市人民建”也就没有任何价值。
社会创新往往在权力与民间相互试探、博弈与适应的过程中诞生新秩序。郑州与开封不是错过了一波所谓的“泼天流量”,而是亲手掐灭了一次基于数字技术开展城市联动治理的可能性。
郑开大道上的每一个数据点都标识出一颗青春炽热的心。笔者此前曾在《“网红文旅局长”的涌现和隐遁》一文中探讨了流量与城市文旅的发展关系。今天更需要说出的是:你不能需要文旅流量的时候就说“年轻人是城市的风景”,而当因为没有预案而接不住破天流量的时候就说他们是“无用的激情”,是无处发泄的荷尔蒙。
至少,郑开大道上的年轻人们,他们用个体的无意义最终成为了集体的“超意义”。只是这种“超意义”是被官方、媒体、参与者以及旁观者各自阐释。
作为数字治理的研究者与观察者,今天我更想探讨开封“共享单车围城”的数治解决路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避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每个驮在共享单车上的大学生在比特世界都是一个“数据包”,数字空间里一个数据点的移动可能是几KB或几个G的流量,而在物理空间中却是50公里的热量与20岁出头的激情。
谁能真正理解那些在郑开大道上飞驰的年轻人呢?他们难道都是贪恋开封景区的免费门票么?那些一生都活在意义之中的人们,谁能理解他们夜骑的意义呢?我想起崔健在《时代的晚上》中这样写道:
没有新的语言 也没有新的方式
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不是什么痛苦 也不是爱较劲
不过是积压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共享单车平台方可能也没有想到,数字平台服务表面上是一种无远弗届的存在,但一旦与现实世界对接却体现出极强的在地性与物质性,不仅平台方的用工、用户以及当地监管措施息息相关,其投放数量、城市秩序影响以及与道路的关系,最终决定一辆共享单车与所在城市的关系。共享单车的服务能力与半径最终是以车轮丈量的,而非以蓝牙和WiFi信号丈量的。
当年的共享单车商业大战最终催生了“共享单车坟场”,表面上是用户争夺战,而本质上是资本站队战。今天郑开大道上的共享单车才真正第一次与用户有关——“远程锁车”——似乎是平台方行使公共空间行为裁决的娴熟手段,虽然是以“根据服务协议”的名义。
为什么提出数字治理路径的推演?因为“开封夜骑”背后本质上与平台、数据与算法支配的数字经济息息相关,因为共享单车这种业态的存在,才会有20万人次夜袭开封的壮观场面。假如需要每个大学生自备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那么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缘起于数字平台生态的问题,可以首先从数字治理方式去寻找解决方案。
个人认为,郑州和开封至少有三次机会避免当前情况的出现。
如果从城市面积、人口、GDP总量和增速来看,开封与郑州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城市。当开封宣布对骑行大学生免票游的时候,理应有一个对城市承载能力的“总量控制”的意识。至少,当骑行的苗头出现,对于郑州大学生、路线与道路流量、开封景区和路线等此类基础数据是可以进行共享的,至少可以推演出可能发生的极限情况。
当骑行人数达到千人规模的时候,可以采用“低数据模式”。在“免票”点燃游开封的激情后,相关部门应该主动与共享单车平台方联合发布骑行线路推荐,对重点路线、景区情况进行提前告知,并在两市交界处节点位置准备启动限流措施。而“远程锁车”在本阶段其实就可以用上,以防止随时停放和超出规定路线窜行。
当骑行人数超过万人规模的时候,此时基本可以采用“中数据”模式,即个人预约制,可每天分时限量放号与放行,对游览景点、停靠地点等进行提前告知和报备,便于城市管理部门提前预判流量,为独自骑行往返的用户提供福利(骑行返回的用户增多,至少可以对共享单车“围城”进行少量疏导),最大限度控制市内单车流量,方便调度。
当骑行人数突破五万人之前,基本可以采用“高数据”模式,即组团出行模式,不提倡单独骑行前往,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优化城市管理、交管部门、文旅部门、应急安全部门的资源配置,减少个体出行的不确定性,并可以尝试在两市交界处提供“换乘服务”或接驳点(提供公共交通换乘),既解决共享单车跨市域出行的风险与监管问题,同时可以阻断对开封城区的拥堵和拥挤。
当然,这只是城市数治的一种理想状态推演,在实施的过程中会牵涉到很多细节。在这起城市公共事件中,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端是热情与积极的开封与郑州大学生们,另一端则是极度“低调”的郑州与郑州高校,似乎直到宣布交通管制的禁令才让人发现郑州的确在“行动”。
从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尔滨冰雪奇缘再到开封王婆、开封夜骑,网红城市的流量经济与文旅生意似乎成为了官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一次隔空致意,成为一种以千篇一律的城市要素展示与意犹未尽的八方来客自拍为核心内容的城市民主实践。城市文旅部门或顺水推舟或主动下场,谁都不愿意因忽视对流量的追捧而被舆论贬斥为“缺乏流量思维”的那个人。
在媒体的聒噪下,迎合流量已等同拥抱未来。似乎,城市公共部门亲自下场制造流量就是正义,就是民意,就是温度,就是知网用网懂网,就是走群众路线。而在一片乐观祥和的流量盛宴下,很少有人关注到背后的风险——随时被网络效应反噬的风险。城市治理资源、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等都是有限的,而比特化扩展的网络协同效应是无限的。开封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如果做一个假设,假设当初“开封夜骑”初具规模的时候,郑州及其高校方积极介入,与开封形成信息互通、数据共享的联动,那么对于这两座城市意味着什么?对那些在路上的年轻人们意味着什么?不过这只是假设,时间窗口转瞬即逝。所有的激情与惋惜都只能停留在时间的无意义流逝之中。
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两座城市联动起来本应该成为皆大欢喜的好事但结果却没有做或以一纸禁令暗示“不值得做”呢?说到底,自组织的共享单车“围城”导致的城市运行冲突治理成本太高,不可知的社会风险无法预估,又或者,笔者暂且发一点“诛心”之论吧:被打上“穷游”标签的年轻人们除了激情还有什么呢?况且我们已不需要这么多激情。
我想起最近在一个会议上听到某位智慧城市专家的观点:
「谁有权定义问题,最终将决定以什么方式和工具来解决问题。」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