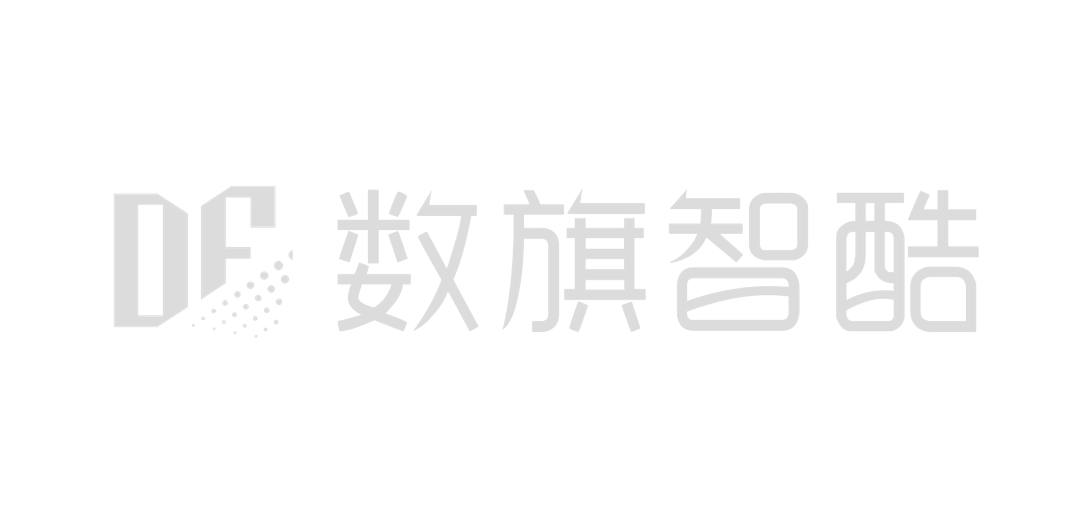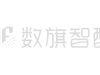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本文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立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3〕29号)的解读文章
从2016年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指导意见【1】,到2018年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文件【2】,再到最近发布的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文件(下称“29号文”)【3】,基本可以视为我国数字政务服务从“能办”、“易办”迈向“好办”的发展过程。其中,“能办”是政务服务内容数字化的过程,“易办”是政务服务获取能力与成本的问题,“好办”则是政务服务的品牌影响与应用效果兼具的表现。
笔者认为,在当前时间节点上提出“建立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至少包含以下几个背景因素:
其一,后疫情时期的政务服务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在疫情期间的高密度高频率服务需求冲击下,后疫情时期的政务服务正在享受着高速发展带来的创新成果,同时也在经受着“变速发展”带来的隐忧。在非常时期“特事特办”背景下的政务服务创新探索,能否找到转型常态化发展的路径?有地方提出的健康码“转”城市码可能就是其中一个缩影。此外,后疫情时期的政务服务发展是否依然具备某种创新自觉与效能提升的自我预期?这也是由发展环境变化投射在政务服务管理者身上的影响因素之一。
其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能力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历时四年时间,目前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作为一个服务用户超过10亿人的国家平台,在具备应对和承载海量用户服务诉求的基础和条件下,需要考虑的已不只是考虑如何触达增量用户,而是如何提升存量用户的黏性,如何建立可靠稳定且值得信赖的用户连接。因此,通过建立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本质是一种持续为用户创造服务价值的方式。
其三,“数字形式主义”在影响政务服务效能预期。“数字形式主义”的背后隐藏的是对数字化改革的价值与成果本末倒置的显性反映,大家看到的或许都是数据造假、重复填报、“表哥表姐”等现象,而真正需要反思和深究的是如何以制度优化来杜绝无意义的行政资源空转。因此,基层作为最终端的执行主体而言,以无感评估、实时监测等方式进行评估考核,减少因为程序本身带来的繁冗,减少以减负的名义增加基层的负担,背后也必须依托常态化工作机制作为保障。
如何理解29号文对未来政务服务发展的影响?笔者认为,除了用户获得感、需求导向、服务反馈、运营保障等方面的发展指引之外,以下四点可能是未来政务服务亟需拥抱的四大变化:
01.从“平台叙事”到“制度叙事”的切换
从“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伊始,我们的数字政务服务发展就一直处于“平台叙事”的旋涡。我们将政务服务网、政务服务App、小程序、自助政务服务平台等同于数字政务服务的改革和创新本身。所有的“数字鸿沟”及“数字形式主义”问题,其背后都是被“平台叙事”所左右和支配。原因在于高速发展的平台经济所教育的用户习惯,让从业者、开发者和研究者也习惯性地认为,商业平台的“用户思维”可以照搬到政务服务领域。互联网平台上的用户运营奇迹也让政务服务平台的管理者叹为观止。
基于网络平台的用户思维介入数字政务服务运营,不仅让政务服务管理者感受到来自公众侧的正反馈,同时,在服务的设计和供给上也可能不自觉地进入商业平台的运营逻辑——即只有“用户”,没有“公众”。
29号文从办事堵点发现解决、服务体验优化、平台支撑能力提升、效能提升保障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工作机制和要求,标志着我国数字政务服务发展正在由“平台叙事”向“制度叙事”切换。要真正发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支撑能力,需要推进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以及国家层面“一网通办”相关法规制度的研究,以此固化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经验做法,使未来的政务服务真正实现“一地创新、多地复用”,而不只是一种特例或盆景。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各地政务服务的探索重点或将不再是通过平台、技术等方面的累积叠加,而是通过制度法规层面的创新求解。
02.从“标准化”建设向“在地性”建设的倾斜
在《A City Is Not A Computer》这本书中,作者指出,数字化技术用标准化与同质化掩盖了城市治理与服务的个性化与多样性。而更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谈论数字政务服务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基于平台的体验、数据的应用以及交互的便捷性等,而非基于我们所处区域或城市的气候、文化、语言、风俗、民族等情况。这种单一的评判标准也让我们对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进行了价值混淆,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单调的审美。
29号文提出,加强一体化政务服务工作联系和创新示范,建立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应用基层联系点,注重发挥市县级平台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中的作用。一方面这不仅是在修复过去几年高歌猛进的数字政务服务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在网络之外被忽视的真实关系,另一方面也将为个性化与多样性的服务需求存在与供给提供更好的接触点。
因此,关于“线下政务服务大厅或政务服务窗口是否会消失”的讨论可以休矣。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线下,而非线上。就像一位专家在谈论大模型的时候所言:我并不担心大模型取代人类,因为技术史的发展证明这没有可能性。我担心的是人类因为技术驯化的沉溺或懒惰最后心甘情愿地龟缩在数字空间而不愿意面对真实世界。
03.让政务服务领导者“把自己的手弄脏”
奥巴马政府的CTO副手珍妮弗·帕兰克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Recoding America》中指出,公共部门花费在政策文件文书设计上的时间远远大于它们面向公众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的时间。而当数字化转型的收益逐步流向了精英人群——比如大企业有专门部门服务,比如商业精英有专人服务代办,而政策设计者又无法理解和经历普通人的办事痛苦过程,最后,数字化其实是在服务的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筑造了一道无形但密不透风的墙。
“我陪群众走流程”的本质就是让决策者与管理者从繁冗庞杂的行政事务中真正走向群众——走向文山会海之下最终面向公众的政务服务产品。笔者曾在某个地方宣传的“厅局长走流程”的电视报道中看到这样一幕:领导一身行政套装坐在办事人员侧面的一把椅子上或询问或指点,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工位上战战兢兢地敲击键盘,办事群众在他们的对面不知所措……不知道这样的“走流程”体验跟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也很怀疑这样的“我陪群众走流程”的领导能走出什么样的流程。
29号文提出,鼓励政务服务部门负责同志走进政务大厅、登录办事平台,看政策“懂不懂”、流程“通不通”、服务“优不优”、体验“好不好”。让领导者“把自己的手弄脏”当然是深入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是真正从自身的决策设计到基层的具体执行之间定位问题所在的重要途径。但值得注意的是,领导亲自走的“流程”,到底是“真流程”还是“假流程”?因此,笔者建议在“我陪群众走流程”的领导完整体验整改完成后可以再来一轮现场回访或“暗访”。
04.走向数字政务服务的“品效合一”时代
“品效合一”是一个商业词汇,简单来说就是“既要品牌声量,又要产品销量”,或者说“叫好又叫座”。但是这种功利性的认识也为人所质疑,即品牌除了营销价值,当它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还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比如苹果公司1997年发布的广告片《Think Different》,随着苹果产品的风行,它已经影响了几代创业者的价值观,成为一种时代的共同情感与社会的群体认同。
29号文提出,切实将企业和群众经常使用的高频服务打造成为“好用”、“爱用”的精品服务。加强政务服务创新先进经验做法总结,建立经验推广常态化机制。建设数字化创新应用案例库和应用推广中心,对地方和部门服务优化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推广和共享应用。完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宣传推广矩阵,多样化展示和推广“一网通办”服务应用,便利企业和群众了解和获取政务服务应用。由此可以发现,数字政务服务的“品效合一”时代正在来临,一项真正值得推广复制的精品政务服务,一定是既有品牌影响又有群众口碑的。
当然,政务服务效果很好理解,可以从流量、下载量、数据量、交互频次等很直观地看出。但政务服务的品牌影响如何理解和评价?笔者认为,当公共服务部门接受了“政务服务品牌”的必要性,即是接受了一种被公众检视和服务监督的邀约。政务服务品牌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品质的承诺,是一个组织的治理能力与行政文化的外化。政务服务品牌建设不仅是广泛触达目标用户的手段,同时也是真正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并实现了“好办”目标的自然反馈。
政务服务品牌不仅是新时期政务服务机构与公众、企业沟通的载体和平台,同时也是在新闻通稿这样的“硬性直给”之外,以案例解读、服务攻略、体验参访、视频直播等方面综合性输出,实现公众对政务服务效能的确切性感知与泛在化连接。总之,政务服务品牌的实质是创造公众自我表达与共情的机会,而不只是传递政务服务机构的声音。
本文提到的文件:
【1】《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号
【2】《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27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立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3〕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