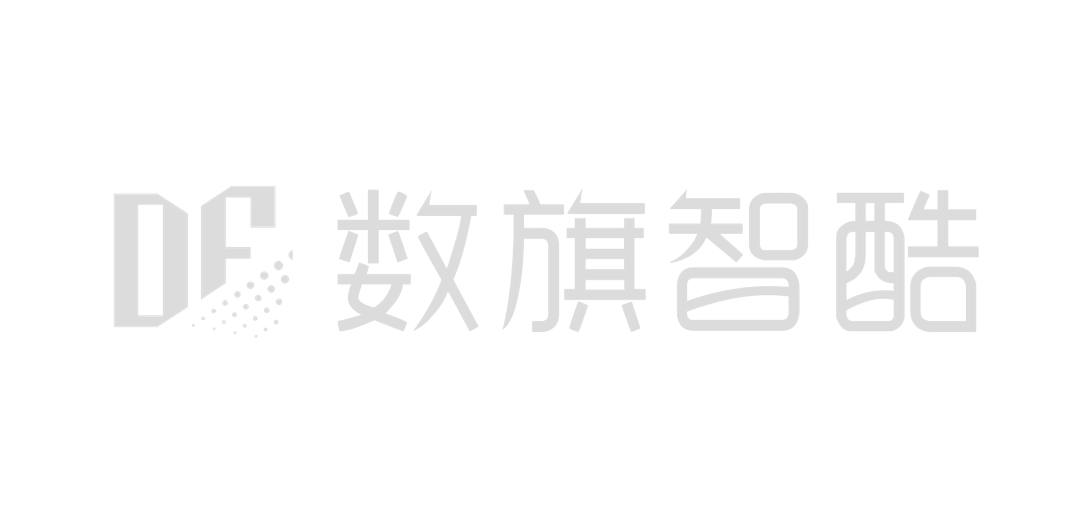作者丨冯 奎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唐 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纵观城市化与数字化的互动进程,城市的数字化发展史是一个从空间到内容、从产业到文化、从行为到制度等要素的持续演进过程,从空间规划、商业活动、治理行为到组织体系的城市数字化渗透。首先是在空间层面,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相互交融,使城市的空间价值、功能、内涵均发生了改变;其次是数字化对城市产业经济的渗透,使数字经济的运行模式、商业模式、体验模式渗入城市运行的方方面面;再次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倒逼和驱动了城市治理行为、规则与制度的转型,治理的工具、对象与模式均发生了改变。最后,城市的数字化生存,本质是基于城市治理组织的数字化思维、体系与框架的生存,是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01.数字政府与城市治理
城市政府一直是推动城市治理与服务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城市运行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数字政府的发展,数字化对城市政府在治理能力、服务模式、监督方式以及评估手段方面的升级再造,使平台、数据、算法成为影响城市运行秩序的重要因素。
自90年代初发轫的政府信息化进程开始,数字政府已经和正在经历着从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到组织数字化的历程,在信息数字化阶段,主要依托于政府内部系统服务于政府内部工作,以信息的无纸化、电子化为主要特征;在业务数字化阶段,主要以服务公众服务体验为核心,以政府机构从决策、治理、服务、监管等业务的在线与连接为主要特征;在组织数字化阶段,主要依托数据要素驱动,变革和重塑政府权力运行流程,创新政府组织运行模式,数据要素由一种政府治理资源转换为一种政府创新的驱动要素。
数字政府主要从三个维度驱动城市治理变革:一是数字政府的组织范式推动了城市治理的决策方式变迁,韩国首尔的“市民即市长”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即是最典型的代表——通过城市数字化治理平台的构建,实现从市长决策、部门响应、市民行动与参与的全流程数据贯通。对于中国而言,近年来活跃于全国两会前在中国政府网及各地省市专门推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我来写”活动,其背后则反映了市民参与城市未来发展决策的重要趋势。二是数字政府的运作工具推动了城市治理的协作方式变迁,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在城市应急事件与日常运行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比如厦门、广州等城市通过“随手拍”的方式举报违章停车,北京、武汉等城市通过移动政务服务平台邀请市民参与发布城市内涝地点,以便市政部门的及时处置,上海、杭州等城市推出城市垃圾分类的专门数字应用,以帮助和引导市民的环保行动。三是数字政府在缩短政民的互动流程与提升公众参与效率,比如近年来中国政府网推出的“我向总理说句话”、各地政务公开平台推出的“市长信箱”以及个别地方的城市政府主管领导通过网络论坛、微信、微博等对热点事件的回应,这些现象的出现充分说明,城市治理与服务议题正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汇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互动的洪流当中,而非传统视野的所谓“政府职责”或者“部门职能”。
数字政府的建设与发展为城市治理应对提供了更为丰富、创新的治理资源与工具,同时,政府机构本身的角色在“城市即平台”的语境中也发生了改变——由传统视野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主体,成为与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并行的主体之一,特别是在面对城市新物种的快速成长趋势下,城市政府机构的数字能力、数据思维与数字治理构建能力,直接影响的了城市的价值选择与发展质量。比如近年来各地城市运管部门对网约车的政策制定、对共享单车投放的监管、对网络外卖平台的管理、对非法网贷平台的打击等,如何在包容审慎监管的背景下支持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同时规避和杜绝城市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这是对数字政府的发展水平与能力的重要考验。
数字政府在城市服务范畴内的具体实践被总结为“网上办、移动办、就近办、自助办”,在城市治理领域则被概括为平台治理、数据治理、协同治理。2019年,上海首次将数字政府建设总结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城市治理“一网统管”,本质是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对城市与城市治理的全新认识,将传统视野下的技术思维切换为一种面向城市未来的“组织技术”——“一网统管”是以人为核心,以数据要素为驱动,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协同,从技术、资源、组织等层面重构城市运行体系的数字时代城市发展理念。目前,以“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为主要理念特征的城市数字政府建设推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的跟随与推崇。
02.数字经济与城市竞争力
数据要素正在成为与劳动力、资源、资本同等重要的市场分配要素。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治理构成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成为当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与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数字经济增速达到GDP增速3倍以上,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其中,广东、江苏、山东等13个省市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北京、上海数字经济GDP占比超过50%。
数字经济裹挟而来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平台效应等对城市竞争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城市产业经济运行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与资源诅咒,打破了依托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获得发生先机的传统竞争位势,使一些工业时代的没落城市、后发城市获得了换道超车的机会。数字经济对城市竞争力提升的最大杠杆作用在于,它使城市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网络节点,推动城市依靠自身的发生生命力、治理能力、服务水平以及文化特点,参与全球网络分工与物流供应链协作,并吸纳全球资本进行本地创新,推动本地创新通过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实现放大效应。本质而言,数字经济的渗透与发展,对城市自身的产业属性、竞争根基产生了一种“转基因”效应——通过数字赋能改造城市发展基因,从而获得新的发展先机与动力。在中国最为明显的是,大数据产业使贵阳这样一座中国西部的边缘城市在过去几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瞩目,成为苹果公司在中国落地的本土数据中心,而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乌镇则由一座位于中国江南水乡的古镇而成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趋势洞察的窗口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对城市竞争力最为明显而直接的推动力。
数字经济对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其背景在于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迁移,推动中国进入“互联网下半场”——从消费互联网进入到产业互联网,由原来依靠资讯、娱乐、游戏等数字消费服务的纯线上经济,转而进入互联网与线下生产、管理、营销、售后等各个流程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C2M模式、智能工厂、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成为热点话题。数字经济改变城市竞争力的基本逻辑是,从数字化开始从提升生产力进入到重塑生产关系范畴,机器成为劳动力参与智能生产,数据成为创新城市运行模式重要燃料,消费者由产品使用者变成产品设计者。来自线上线下的市民倾洒在数字平台的认知盈余成为一座城市在数字时代赖以生存以及极富生命力的源泉。建立全网协作网络、汇聚全球资源能力、塑造全时运营体系等成为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竞争力升级的三个关键维度。
从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通过各城市的发展规划、行动方案与新闻报道可以获知,以杭州、深圳为代表的城市,在移动支付、数字生活、智能制造等领域获得高速发展,并陆续培育了阿里巴巴、腾讯等这样影响世界的顶级数字经济企业;以贵州、合肥、成都、长沙、南昌等中西部内陆城市,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游戏、工业互联网、智能驾驶等领域均打造了具有自身城市产业特色的独角兽企业,并持续引入国内知名数字经济巨头总部,大力拓展在区块链、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规划,搭建大数据、互联网、VR(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行业峰会平台,吸聚全球数字经济人才与资源,以培育数字经济生态。
数字经济不只是在城市就业与GDP贡献上提升城市竞争力,更是从城市服务能级、治理工具与产业创新上重塑城市运行秩序。随着城市政府数据开放程度的逐步扩大,数字经济创新企业通过开放数据进行产品应用研发以解决城市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互动的重要趋势——数字政府向社会开放公共数据,数字经济利用城市数据资源研发应用帮助政府解决城市问题,并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最终以多方共赢的方式长期稳定地解决社会问题。诸多城市开始陆续加大引进和孵化培育数字经济企业的力度,并将具有代表的数字经济企业作为城市发展潜力的标签与指针,视为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与拥抱数字经济的定力。
从数字经济业态来看,以途家为代表的共享住宿平台,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社交电商平台,以叮咚买菜为代表的生鲜平台,均是生长在城市内部,从解决城市市民住宿、购物、生活问题出发,最终成长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与创新力量。
03.数字素养与城市型社会
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发展,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构成模式,从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现代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到数字化叠加城镇化的“数人社会”——人成为数字平台与设备的操控者与使用者,也同时成为平台数据的一部分。人同时存在于城市空间与网络空间当中,并在数据流动与需求变迁之下穿梭于两个空间的中心与边界。
从社会层面而言,城市的数字化生存有赖于政府、企业和市民的数字素养的提升,首先从政府侧而言,政府公共部门在决策、治理、服务、监管等过程中,非常娴熟地采用数字化应用与工具,并为市民办事提供网络化、智能化、自助化、移动化的政务服务平台,大大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运行效率;其次从企业侧而言,通过数字营销、管理与售后服务流程,从而快速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从客户发掘到产品创新的全过程均通过数字化工具进行支撑;再次从市民角度而言,依托了移动支付、手机扫码、地图定位、网络打车、网络外卖等数字生活服务正在成为市民生活的日常。在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进程中,在城市治理与服务的资源、需求供给的互动及对撞中,政府、企业与市民在不断实现对数字化的认知升级,并逐渐习得自身在数字时代赖以生存的技能,沉淀而成自身应对和拥抱数字时代的数字素养。
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市型社会的快速形成,一方面将不同阶层、领域、背景的人群迅速“改造”为“新市民”,另一方面又因为数字素养的高低不一形成了现实中的“新数字鸿沟”,且这种所谓的“新数字鸿沟”表现为从数字技术及设备的“获得不平等”走向“使用不平等”,以及面对数字网络应用的“克制”与“上瘾”之间的差别。数字素养正在成为取代职业类型、经济实力以划分城市阶层的重要影响指标,对于以新新人类为主体的数字原住民而言,数字素养决定他们可以快速、高效地获得自身的城市生存权利,比如公共出行扫码、便利店移动支付、游乐园网络预约等;而对于失去对数字化应用的学习和感知能力的老龄人群而言,则会因为不懂得使用智能手机而失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权利。为了提升城市发展温度与数字化普惠能力,在城市疫情防控形势尚未完全缓解的时候,无锡市在高铁站率先为老人设置了“无健康码通道”,郑州市在机场则设立了“老年人入郑扫码帮扶点”,杭州则针对部分低收入人群、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存在“被数字化”的困境,通过《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草案)》立法,规定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确保决策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透明公平合理,并完善线下服务和救济渠道,保障公民选择传统服务方式的权利。
随着城市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公众的数字素养正在成为影响城市发展质量与后劲的重要因素。在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治理理念牵引下,公众的在线参政议政能力、城市服务数据的“喂养能力”、城市发展在线议程设计能力等成为城市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良好的市民数字素养正在成为城市治理、服务以及产业创新的新生力量。
04.技术赋权与数字道德
城市的数字化生存集中表现在数字技术对于城市公共部门与市民群体的双向赋权: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城市治理与服务能级,以实现更好的城市运行效率与人居环境;通过为公众在城市决策、治理、服务等过程中的参与能力与机会赋权,从实现“人民城市”的愿景。
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正在成为重塑城市运行秩序与竞争力的关键支撑,在城市环保、交通、物流、安防、教育等领域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通过物联网感知设施对空气质量、水质土壤以及街道噪音的监测,可以准确评估目标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通过利用交通大数据对早晚高峰、重要路口等车流量的监测,可以分析和优化城市交通规划;通过对敏感区域、敏感人群以及公共场所的智能视频监测,可以分析、预测和定位敏感人群或犯罪嫌疑人,这些都是通过数字新基建支撑和推动实现的城市治理新场景,对优化城市管理资源与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工具化特征正在减退,而生物化特征日趋凸显。正如BBC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所言,“我们已经走过以工具为基础的技术环境,来了以致瘾和操纵为基础的技术环境,技术不再是等待被使用的工具,它们都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办法去实现这些目标,利用人的心理来对付人。”因此,新兴数字技术确实在驱动城市运行效率与质量的提升,但不可忽视其正在被异化的一面。比如人脸识别由于其关乎隐私安全的风险,美国部分城市如旧金山、加州、马里兰州等陆续推出了法律禁止条令,而在中国城市则在高铁站的公共卫生间免费取纸装置也设置了人脸识别摄像头;此外,以升级城市路灯为目的的智能灯杆在美国城市圣地亚哥遭到了市民的反对,其原因在于其通过视觉、听觉传感器对公众隐私的监测和收集引发了担忧。
对数字时代的城市发展而言,技术赋权不仅是指对城市公共部门的赋权,也包含对市民个体的赋权。《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在《疫情中我们将创造怎样的世界?》一文中表示,“我们当然应该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力。当人们谈论监控时,请记住,同样的技术,公共当局可以用它监控个人,个人也可以用它监控公共当局。”但由于法律制度规范与个体数字素养的影响,技术赋权对公共部门的价值与力度往往超过个人,在由数据、平台、算法驱动的世界里,越来越难看到在网络BBS时代个人通过论坛一个网帖而成为撬动公共部门行动的杠杆,技术在向个体进行赋权的同时,也以加速信息流动和注意力迁移的方式,加速了信息沉没与更迭的速度。
相比“古典互联网”时代,智能化时代谈论技术赋权的最大差异是,以人为核心的数据越来越具有唯一性,包括指纹、声音、人脸等生物数据,原来依靠个人邮箱、IP、账户名等已无法定义个人画像,生物数据的采集使数字空间对人的需求判断与感知越来越精准,从而也加速了风险的集聚。因此,在城市视角下,以保护人的隐私与基本权利为核心,围绕公共部门的决策行为与数据开放,建立以数字治理、服务、监管等为主要内容的数字道德框架,这对于进一步推动技术赋权以提升城市发展潜力显得至关重要。

本文节选自《数字治理:中国城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