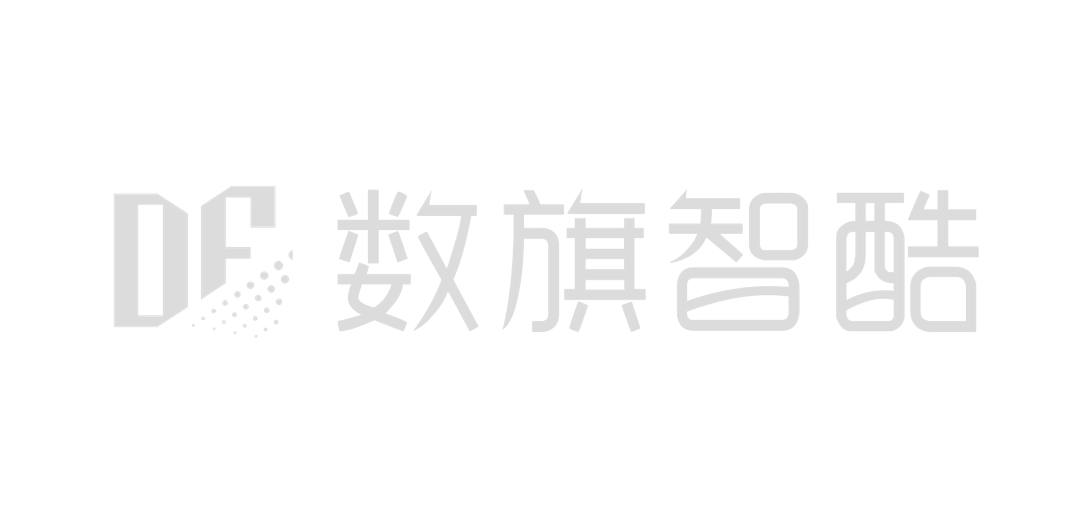本文为数旗智酷创始人唐鹏对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教授领衔的《中国城市数字治理发展报告:城市数字治理的盼与忧——走向善治》的点评。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对这份报告的三个观感:
○ 报告以非数据的感性表达,对“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数字治理”回答得形象且具体,也表达了依靠数据可能无法完整呈现的观点;
○ 报告摈斥了一般研究对现状、趋势、建议等写作套路,直击问题核心,真正从市民和用户角度来看城市数字治理的影响;
○ 如果将我们的观点变得“可执行”,那么,我想这份报告可以试图成为城市数字应用开发的设计价值观、数字伦理守则甚至道德指南。
我理解的“城市数字治理盼与忧”所要表达的四个核心问题
世界的“标准”与我们的“非标准化”:标准化、规范化似乎历来都是我们理解数字化的“代名词”,从充电接口到智慧城市系统,统一的技术标准才是这个世界得以连接和运行的基础。在很多文件、方案里,我们都以标准化、规范化为数字化建设的目标,但“非标准化”才是我们的生活。数字化能带来我们效率,但数字化同样忽略掉了的这个世界细微的参差与不同,这些才是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这也是报告中指出我们期盼的城市数字治理需要“量体裁衣”的因由。
“人有人的用处”:《人有人的用处》是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诺伯特·维纳的著作。数字技术其实是最适合“一刀切”的技术,规范性技术的实施可以迅速创造一种整齐划一的秩序感,但也包裹着不堪一击的脆弱性。要想不走向“一刀切”,就最大限度地要发挥人的作用。而通过个体感受来评判一个应用、制度和措施的好坏,而不是依靠看似言之有据而其实可能大而无当无法准确定位到人的感受本身的数据,这是我们可选的路径之一。当然,如果我们都试图依靠数据来呈现城市治理的优劣,那我想,人在城市治理中是不是就可有可无了?或者连配角也不是?只是一个配合城市运行的参数?因此,在一个因为新兴数字技术广泛深入应用而导致城市治理变得无序、混乱的熵增过程中,人必然成为提升城市数字治理的秩序感、组织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推动力量。事实上,在数据导向、大屏装上的城市数字治理现实语境中,“人有人的用处”正在被挑战。
“‘迭代’的非必要性”:数字化的“迭代”代表着升级、更新,只需要修改一行代码,就可以变得与众不同,变得超越过去。但人的生活场景与习惯的“迭代”是一个漫长的摩擦过程。并且,我们也有拒绝“迭代”的需求,比如老龄人群以及阳性人群。比如登机需要48小时核酸报告,但就因为飞机延误导致核酸报告过期2分钟而无法登机。城市治理中的偏见会有很多,但我们不应该通过数字化的应用去加强和固化这种偏见,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的,但我想没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变得“截然不同”。当我们适应一种生活可能是不希望快速迭代的,那种急速的幻灭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承受的。
“个体需求的尊严”:毋庸置疑的是,当下我们的城市数字治理应用的设计、逻辑及价值观,基本上衍生于商业互联网应用的源流,从建设到运营,所谓“用户活跃率”、所谓“用户至上”、所谓“体验为王”等等,均是被商业互联网驯化的腔调。而对于商业互联网平台而言,对信息的噪音、数据的冗余以及非目标用户需求是可以完全忽略的,但对于一个2500万人口的城市数字应用而言,在疫情封控期间只要有一户无法获取食物或某一位慢性病人得不到救治,这都是天大的事情,这是无法被忽略的,这也是商业数字产品与公共数字产品的区别。商业价值最大化和公共服务平台的普惠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之所以看到有些城市政务平台在运营上出现一些怪异的“招数”,其背后原因也在于此。
城市发展规律与数字化演进规律是否是背离的?
数字化永远向更高更快更强升级进化。我们的软件、电脑、手机都是不停地升级到更高版本。而城市是有自我的兴衰逻辑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会像数字应用或者软件平台一样,每周更新一次,每月更新一次。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城市可以永远都是新的,城市是会衰落或波动的。有的城市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比如庞贝古城、千岛湖水底下的淳安古城。有的城市则穿越历史永存,并继续引领和代表着某种时代的风尚与先进性。比如《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所描述的杭州那时就已经有先进的卫生排水系统与消防安保系统。
在大众传媒中的“数字化”一直在向自助化、智能化甚至无人化高歌猛进,而“机器是否取代人”的讨论也层出不穷,似乎在强大的数据和机器面前,作为主体的人似乎也对自我的存在价值已不够坚定,并被数字化的魅力所迷惑与引诱。但城市是离不开人的创造和聚集的,目前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记载过某座无人的城市如何繁荣与自我繁衍。我们已知的也只是因为人类的贪婪而建造的“鬼城”。
数字化的流量逻辑与城市的流量逻辑看似一致,但其实千差万别。数字平台是先有流量,后有商业模式,所谓“得流量得天下”、“得用户得天下”都讲的是这个道理。而城市是先有地段,后有流量。虽然,数字化让城市的物理地址在数字平台上进行了价值重塑,甚至出现“无法被搜索则等于不存在”的数字空间“倾轧”物理空间的现象。但是,不具备物理空间优势的城市或城市单元会因为数字化的流量迅速膨胀,然后会因为无法承载和消化流量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商业能力,而最终泯然众城。这一点后果在团购兴起而无限制接单的街边小店身上发生过,也在不少网红城市的文旅场景中发生过。
我特别赞成报告关于城市数字治理应该“细水长流”,而摈斥“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从城市的发展史来看,我们看到一些逐浪而行的城市,主政者或操盘者懂得一座城市的文脉传承需要时间,一座城市的产业生态发展需要时间,但是唯独对数字化的发展极为缺乏耐心。所谓互联网思维的“颠覆”观念,以及“一针捅破天”的产品思维,多少给了需要长期主义的城市数字治理一些急功近利的非分之想,而这些与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相违背的。
在城市数字治理过程中,“用新技术来实现旧理念”有时会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以健康码在三年以来的发展演化为例,最新出现的“离X码”其实已经成为了古早时期“介绍信”的数字化复刻版。这会带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刺激:如果数字化的存在就是为了将一种陈旧、复古、不适的治理模式变得更高效,那么我们最终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对数字化介入城市治理已然不是简单的爱或恨的关系,数字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正在浮现。以近期南方某市为例,一队打工人在台风天下排队做核酸,风雨越来越大,防疫工作人员怕发生安全事故,于是决定停止采样。但是,现场所有打工人不同意,坚决要求继续做,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如果没有核酸报告,明天很可能就进不了办公室。于是,防疫人员只好一边抓着帐篷别被风吹走,一边继续核酸采样。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方是享受和愉悦的,但现实让他们不得不委身于此。
正因为这些现象与担忧的存在,并且,在历经三年堪称“迎头痛击”般的城市数字治理“灾难性”事件,我们依然未曾拥有可持续应对的办法与法治层面的共识,又如在公共舆论层面,很多问题的出现尚存在认知的盲区以及莫衷一是的各方解读,所以,我觉得这份报告出现的时机与关注的问题均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