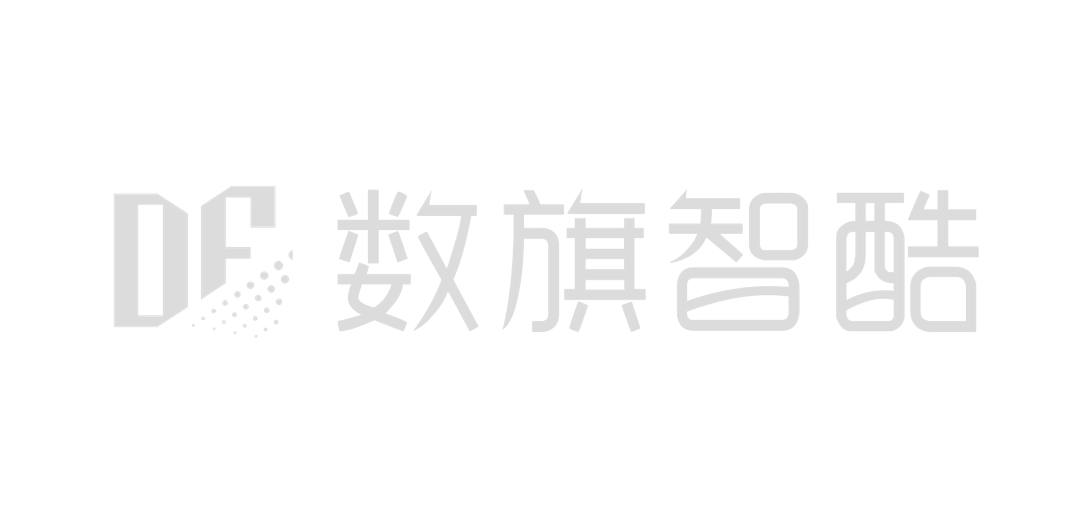撰文:唐 鹏
为什么要推荐《赛博朋克·边缘行者》?
因为它隐喻了一个我们正在坠落的“数字炼狱”而又无法拒绝的可能未来?

《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小镇做题家上不起贵族学校退学后如何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一个超级打工人的故事。而其内核是下沉时代中的个体独自倾诉的一曲挽歌,是一部赛博丛林里的“盗墓笔记”。
导演今石洋之与主力编剧大塚雅彦合作过《星球大战》、《新世纪福音战士》等经典动画片,从本剧集中也可以看出,赛博朋克们的世界有深重的日本隐者和浪人文化的烙印。不知道编剧或导演是否受到过中国香港武侠剧的影响,剧中的主人公大卫俨然像《神雕侠侣》中掉入山洞捡到武侠秘籍的杨过,连身手都让我想起“降龙十八掌”的阵法。
《赛博朋克·边缘行者》是一个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杂糅体,像一个映射政治、商业、技术、治理、社会的多棱镜。

主人公是在“夜之城”上贵族学校的大卫,他的母亲在一场偶然的街头火拼中意外去世,大卫获得了遗留给他的一个名为“斯安威斯坦”的军用“义体”,从此成为“夜之城”几乎最能打的赛博朋克。没人想到这种特殊的军用“义体”能够被他一天用八次而不挂掉,直到他流鼻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需要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义体”对身体的侵蚀。而“免疫抑制剂”用多了将会“抑制人性”。
“抑制人性”——这应该是数字化原教旨主义者最不忍启齿的一个话题吧。问题是,当有一天,我们身上的金属和电路板多于血肉的时候,“人性”还有存在的余地么?“强大的义体将灵魂从肉体抽离,灵魂会置于机械之中落入虚空的边缘”。人性与灵魂,这本应该就是赛博空间排异的东西吧?不然,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直播间等着看人自杀呢?
“夜之城”是一个依靠充值而得以延续的世界。水、电、房租、洗衣机等没有充值付费将会自动停止、锁门和停止运行。大卫作为一个被送入贵族学校的单亲家庭男生,被他母亲寄望的是通过学习努力,不断奋斗,从而进入“夜之城”的公司精英序列。是的,大卫几乎代表了每一个县城母亲对孩子的渴望——送入民办私立学校,希望他们成为“人上人”的精英,成为顶级打工人。
但是,很遗憾,在一个被公司统治的城市的“第四次公司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这些被装入“义体”的打工人最终没有成为精英,而是成为精英被用来反复测试“义体”数据和应用极限的数据载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具人。是不是很像我们当下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将人作为数据”的瞬间?那些在任何公共场合装个摄像头贴个二维码就让人刷脸和扫码的地方,那些在八线小县城为一袋米一瓶油而在摄像头前面贡献人脸数据的中老年家庭妇女,就是另一种方式存在的“大卫”。

《赛博朋克·边缘行者》描述的是一个“公司主宰”的世界,一方面我感觉是主创对当下全球政府对科技巨头监管和治理智慧的无能所表现的不满,另一方面我觉得又像一种对“公司主宰世界”所造成灾难的恐惧与服从性写照。
“公司”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物种,在剧中似乎暗示着人类社会从城邦、国家到公司是一种硅基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演进路线。但是,公司不仅影响现代社会的根本秩序,也控制着赛博空间的根本价值,以“超梦”,以“义体”。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表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革新都是在公司,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产生的。《赛博朋克·边缘行者》向我们展示的是,“公司”已成为一种不仅具有商业目标,同时具有城市政治野心与权力企图的赛博化怪胎。这种艺术表达的危险性也投射到了现实,比如Google的创始人之一布林就在《Bit Tyrants》中说道:“如果世界各国的军队都与Google这样的国际组织合作,而不是与民族主义的国防承包商合作,对和平会更有好处。”如果对照荒坂和军用科技公司在剧中的作为,我们就可以理解布林是何等的狂妄与鲁莽。

荒坂和军用科技两大公司主宰了“夜之城”,它们之间的争斗和杀伐也裹挟了整个城市的所有人。唯一代表公共权力的是“暴恐行动队”。厮杀和清除成为一种城市日常生活。只有被认定为失控、发疯或者“义体”出现程序紊乱才会被“暴恐行动队”最终消灭。
“荒坂公司的目的是挖掘旧网中的数据价值,那些留在历史空间中的遗产,海量遗失的信息和知识。”每一个如大卫一样在“夜之城”“接活”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盗墓窃贼,只是盗墓盗的是被称为“古董”的金银财宝以及历史尊物,而大卫们要盗猎的是来自历史深渊的“数字古董”一般的个人生命记忆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可以出售给特定机构定制为“超梦”。这些“超梦”然后贩卖给那些需要的人,他们可以在别人缤纷的人生记忆里畅游。
数据成为“夜之城”的问题,同时也是答案。那些飘忽在数字空间中的数字遗产,就像亟待转世附身的无家可归的灵魂。而荒坂公司豢养的黑客们正是这个隐秘世界的“灵魂猎手”——打捞灵魂,然后售卖给下一个肉身作为“转世灵童”。“灵魂”在数字世界脱离了远古时代那些似是而非影影绰绰的描述,以一种更具象的方式存在。
每一个安装进人体的“义体”芯片都有自动录制超梦的功能——就像人生记录仪一样地录制你的一举一动以及心理活动。而如果对超梦的过度沉溺和使用不当,消费超梦的人将可能“困在超梦里”。超梦即灵魂。

“夜之城”简化了社会的阶层属性,同时又营造了“去阶级化”与“去身份化”的幻境——你所安装的义体就代表你的阶层和身份,“你是谁”只与你的“义体”型号有关。人的情绪和力量完全被精确地量化,人的个性与价值彻底被符号化。当某一天某家公司的机器人承担了家务、养老、健康、工作等内容,那么,“我是谁”也就只与某家公司的产品、文化与价值观有关了。“义体”似乎又代表一种阶层固化与特权隔离的屏障。“夜之城”的特权是不可逾越、无法流动的,因为普通人无法承受特殊义体对身体和神经的损伤。就像一般的拆迁户是无法承受巨量现金的精神冲击,不是败光在赌场,就是都扔在骗局里。
那些没人装过“义体”的“原装人”,在荒坂市政中心地铁站的地下通道里如蝼蚁一般活着。剧中出现过的另一位“原装人”——一位偶然出现在大卫“杀人现场”的戴眼镜的女性,激发了大卫的人性,让他想起了他逝去的母亲。
“夜之城”里复制和继承了所有来自尘世的“现代化成果”,比如权力、阶级、效率、冷漠、暴虐、血腥、自动化等,唯一被延续的“原装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是大卫和露西之间未竟的暧昧情感,他们的理想之城应该是如月球表面一样自由、平静、辽阔,但他们的有生之年只一起短暂地去过一次。直到大卫在最后被“亚当重锤”打败,露西最后回忆的也是那一次月球之旅。
“夜之城”的所有人争取的不是生存机会,而是生存本身。肉体、血液、呼吸、脉搏等对于装有“义体”的“赏金猎人”们其实并没有生物性的意义,唯一有意义的是被插入身体的芯片的计算能力以及续航能力。
大卫没有“超梦定制师”吉黑那么幸运,他没有购买“创伤小组”的VIP服务,所以他无法被“重置”。这让我想起那些因为没有核酸报告而死在医院门口的人,他们似乎也没有获得某种生命延续的VIP认证。
一些人的辛勤劳动就是为了让另一些人获得快乐和快感。或许我们现在还认为这句话存在阶级性,未来我们必将知晓:让一些人步履不停,让另一些人无数事事,这就是智能化加持的社会劳动力结构性变异。看看那些在红绿灯前冲刺的外卖骑手和每天在电脑前死宅的现代人们,大抵就是这样。

“人口老龄化”与“人体硅基化”是同步进行的。
未来,或许我们担心的不是硅基文明如何碾压碳基文明,而是被权力加持的“义体”如何劫掠另一部分“义体”。不错,在一个赛博朋克世界,也是“有钱才有权势”,这似乎让人有些悲伤。但“斯安威斯坦”军用“义体”似乎说明:比特也是不平等的。
大卫和露西坐在远方的山顶看着城市的霓虹灯说,“城市像一个闪烁灯光制成的牢笼”,这似乎像一个工业时代的市民对城市命运的注脚。只是,这个“闪烁灯光制成的牢笼”像磁铁一样源源不断地吸附着资源、资本、欲望和人口。同时,闪烁灯光也在炙烤着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
露西说的那句“月亮没出来,星星才那么亮”,我没看出这句话的哲理,却看到了一个低阶打工人怀才不遇一心想升职加薪在半夜若有所指地发出的朋友圈。“追求的不是自愿的梦想,终于意识到强加的梦想不值得”,这又让人觉得是一个叛逆期少年的觉醒,或是一个青春期行将结束的文艺青年开始与自我和解的伊始。
最后,请原谅我想起查尔斯张的那句名言:这世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年轻人太努力对身体不好。“这世界”也包括赛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