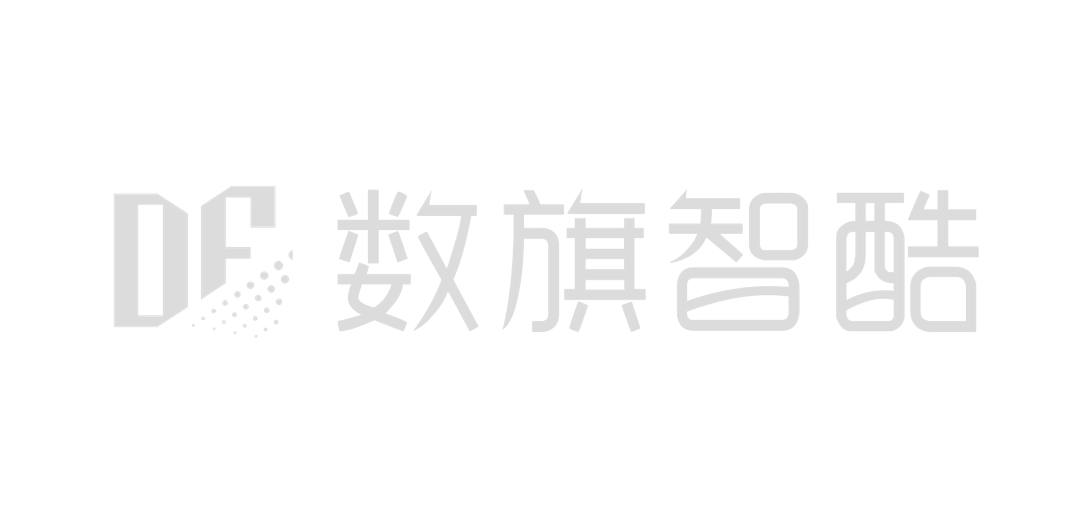撰文:唐 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要求,“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由此,诞生于2020年2月以一种数字治理创新模式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充当过重要角色的健康码正在宣告落幕。在地铁、机场、车站等交通卡口被工作人员撕下来的场所码照片被拍下在朋友圈疯传,一切都似乎在宣告一个无疫的新世界与新秩序的到来。
河流冰封往往是一夜之间,但要全部解冻需要一整个春天。在我们慨叹那种制度的惯性可能无法快速自愈和调整的同时,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解冻的速度也让我们惊叹于其无远弗届的效率,再看来自浙江、苏州、佛山远赴海外抢订单拼经济的新闻,似乎就像30多年来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最新的一次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复兴。
健康码的诞生,使“扫码”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制度,不仅因为“健康”背后的意义而迅速普及推广,也因为“健康”带来的联想而时常遭到非议。作为一种“经典”的嵌入式治理工具,在社会场景嵌入、治理流程嵌入与个体的行为嵌入方面,充满了数字治理应用的所有优点与缺点。曾经作为一个便利防疫通行的网红应用,但由于其在阶段产生的异质性与负外部性逐渐增强,迅速坠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况。
在落幕的时刻来思考健康码给我们的时代和社会留下的遗产,更多的是希望提供应对“乌卡时代”的一种前车之鉴,以及为如何持续拥抱数字时代并为进入元宇宙社会提供可能的启示。
数旗智酷认为,健康码的消亡至少为我们留下了六大遗产。
健康码对数字社会的演进功不可没。如果说新冠疫情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偶然事件,那么,健康码的出现则是一个必然事件,新冠疫情只是将它的发生时间提前了。在公共场所、交通卡点以及区域流动场景中,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强制性、必要、无差别的健康码查验,近似于一场数字社会的启蒙运动,将每一个人卷入到对社会数字化的认识与理解当中来。而在健康码对人脸识别、个人身份数据的整合共享后,因为核酸检测、疫苗接种衍生的失踪人口的找回、犯罪嫌疑人的抓捕等新闻,则侧面印证了健康码在防疫之外的价值。
健康码是一次政务数据产品化的实验。如何将政务数据封装成为好用、易用、爱用的治理应用与服务产品,这一直是政务数据治理领域的重要话题。数据开放也好,数据交易也罢,只有将数据置入目标场景中才能观测数据价值的嬗变过程。而健康码通过将生物信息、身份数据、位置数据以及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数据进行结合,并置入不同区域的防疫场景,真正打造成为了一个小巧而强大的数字抗疫工具,不可忽略其在疫情初期的重要作用。而由此我们也应该想到,大而无当的巨系统、大平台背后,更应该重视以健康码为代表的小切口与轻应用。只是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健康码的易用体验特质,而不是流连于健康码的非凡控制力。
健康码成为推动数字政府创新的杠杆与新起点。从政府数字化转型演进来看,政府网站、政务APP、政务新媒体等都是不同阶段的独立或宿主式的重要载体,承担了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甚至社会治理的功能。而健康码的本质是一种以数据与算力支撑的云服务,高并发、多场景、低延时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数字政府应用,这为未来的数字政府创新提供了更新的思路——好产品的背后是“真需求”,以及可供持续迭代的技术框架与运营资源。健康码之后诞生的“复工码”、“企业码”等只是一种价值有限的克隆,但“码上办”则是在数据与体验层面颠覆原有办事模式的创新。此外,当不少人正在远离健康码因红码、弹窗所产生的梦魇的时候,我们仍需正视健康码因为“旁逸斜出”而无法迅速消除的影响。
健康码的滥用呈现出“数字利维坦”的新棱角。无论是远程弹窗、集体黄码还是群体红码,这都体现出当数字政务服务可以“跨省通办”的时候,以“跨省赋码”为特征的数字管制措施也在轻盈而深刻地高速发展,国家机器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所催生的新型管控能力正在呈指数级上升。健康码不仅成为一种执行管控行为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一种规避主体责任的绝佳对象。由此使个体在遭遇健康码弹窗、黄码、红码后,人不仅在数字空间被放逐,在现实空间中也有家不能归,所能做的只是在电话和数字平台上面对一个虚无缥缈的“上级部门”做类似“对空言说”的申辩。因此,不论是政府、公众还是技术厂商,如果要反思健康码的遗产,可能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数字利维坦”的超能力如何驯服与约束。
健康码必将引发对“代码即法律”的反思。当我们在数字治理领域谈论“代码即法律”的时候,谈论的更多的是希望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对原有的官僚系统的弊病、流程等进行改造,以契合数字化转型的要求。而从健康码的应用过程中可以发现,原有的部门与治理系统往往会娴熟而又准确地选择符合他们所能容忍和认可的“创新”,去修复和说服原有弊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不是去打破和舍弃某些机制来重塑服务。当“代码即法律”塑型为“二维码即法律”,当健康码进化为“场所码”,当健康码红码成为一种病毒的数字意像,除了反思“一切社会要素代码化”是否莽撞外,更需要思考谁有权通过何种程序来发布或修改“代码”。
健康码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的权利”。健康码不仅在疫情防控期间赋予了我们通行的权利,同时也让黄码和红码的用户交出了自己的权利。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中表示,“人基于理性的自我约束特质,被人工智能的秩序设计与程序挤压所替代。”在人的理性和程序的理性之间,从健康码的演进来看,其实是程序的非理性冲击了公众对数字化便利的好感,比如忽黄忽绿的健康码,比如不确定什么时候弹窗的健康宝。疫情防控期间的健康码应用毕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但是当健康码已经假疫情之名而超越疫情的应用范畴被其他权力所征用,那么我们就更需关注在未来的数字化进程中如何设置权力的“防火墙”。
对于政府而言,健康码消失后,可能还有两大问题待解:一是健康码在疫情防控期间采集的涉及个人隐私的高敏感数据信息接下来如何处理?如果不进行销毁,公众是否可以拥有和实时掌握这些个人数据的调取记录与流动去向?二是健康码一度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风口,成为治理、监管和营商领域创新的应用基本盘与创新参照物。当这种褒贬兼有的高频应用标杆逐渐远去,下一步需要如何寻找数字政府建设加速换挡的新动能。
一个好消息是健康码终于要离开我们的生活,另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好消息的消息是chatGPT正在长驱直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一次它不是限制我们的出行,它开始限制只有人才可以的那些思想体操与思维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