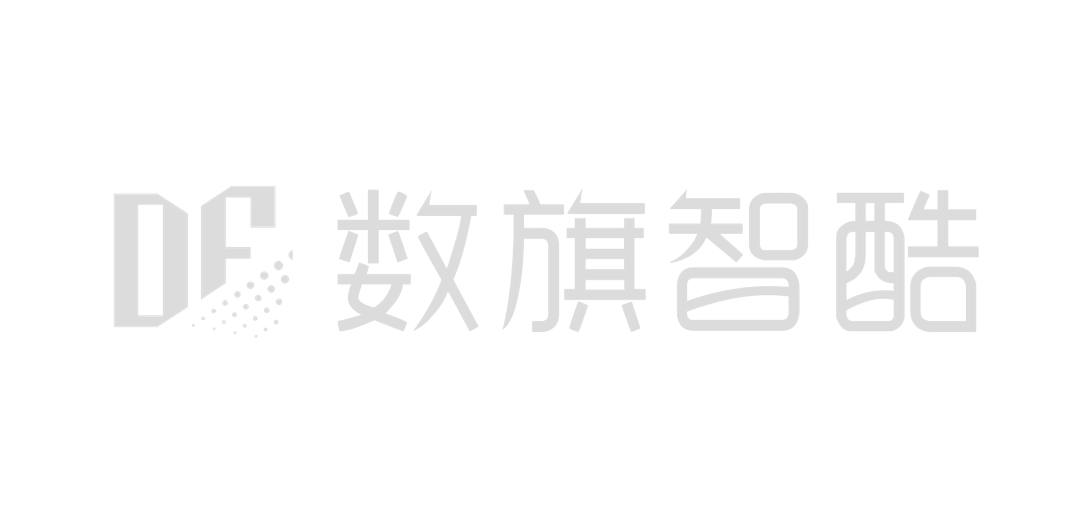数旗智酷首席评论员 唐 鹏丨作者
李 遇丨编辑
读完珍妮弗·温特与良太小野合著的《未来互联网》,心头清晰而笃定地冒出一句话:未来互联网的“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我们都在“昨天”过完了“明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让一切都在被数字化透支与超前消费以及供给,我们马不停蹄的接收和输出数据,机器马不停蹄地自我学习与反馈,一切都在一个被精密计算而颇具预言气质的空间里各取所需。
《未来互联网》一书印证和打破了我们对互联网的诸多幻想或者向往。
互联网告别了线性发展的逻辑,走向块茎革命,爆发式、无秩序、无逻辑可循的创新与发展,被嫁接、被植入、被裂变的新物种将层出不穷。曾经我们寄希望于互联网是一个数字乌托邦,并狂妄而自信地希望建立以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为精神依归的属于自己的“网络共和国”,而当网络谣言、恐怖主义、“转换性障碍”蔓延于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网络游戏等平台。曾经的乌托邦信徒并未向互联网本身需求解决方案,而现实情况也不能指望互联网巨头以及数字利益集团的道德自省,大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政府监管,是的,曾经希望“划网而治”的互联网原教旨主义者在寻求来自于政府立法与权力的保护。
马云在2017年提出“阿里巴巴未来二十年的目标是打造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而facebook与剑桥分析事件告诉我们,超级互联网平台是可以干扰政治选举的。那未来互联网会不会诞生原生的“政治体”?一个超越国别政治利益的宪法体系,一个从地缘政治进化到“网缘政治”的外交格局,一个超越国家实体去治理数据交易和流通的“DWTO”?这一切是可能的么?爱沙尼亚的全球“数字公民”实践似乎已经可以窥见端倪。
在互联网营销领域有个术语叫“病毒式传播”,意思是利用人际网络让营销信息在互联网上像病毒一样扩散,以达到短时间占据人们心智的目的。而社交媒体的发展让用户对在线内容的模仿与学习正在变得普遍,从流行词变成口头禅,到火爆视频被线下模仿,再到蛊惑性、沉浸式游戏让用户不自觉地进行学习与实践,比如一款以青少年玩家为主的“蓝鲸”自杀游戏,已经风靡俄罗斯等数十个国家。病毒传播是一种生理性病毒感染,而网络感染性链接正在通过社交媒体成为一种流行病,跃出屏幕成为一种影响用户生理反应的“转换性障碍”,这种未来互联网的疫情还不能被医学完全解释,还需要法律、心理学的介入。
曾经我们一度认为“数字红利”的获取与受教育程度无关,相比琴棋书画,认为一个儿童与一个博士的数字化设备使用习惯和能力是趋于一致的,所以数字化对于他们而言的积极价值是平等而稳定的。而《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一个叫OLPC(“孩子人手一台笔记本”)的实验性项目中打破了我的这种“偏见”,他的团队在埃塞俄比亚的两个偏远村庄投放了一批预装安卓系统应用软件的笔记本电脑,并跟踪观测学生的使用,大家在接受和使用上都很熟练,刚开始确实对教育水平提升有一定作用,但随后发生了急剧下降。因此他不得不中断了该项目。人与机器的关系,人进入互联网的方式,人进入互联网之后在N个十字路口与诱惑之间的选择,都存在诸多的差异与不确定,机器与人是相互塑造的。
作者表示,未来互联网将是“机器生成见解”,而人在未来只负责给互联网和机器提供信息。这与当下的主流意识都是截然相反的。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主导下,大家普遍认为:只有人才有思想、情感与价值观,机器永远只是人的附庸。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或许只是一台机器的数据饲养员而已,机器生成见解,机器为人类决策,都将司空见惯,看看现在吧,高德地图就在为每一个路盲的司机做决策,未来只会更甚。那么,机器是否会创造一种独立的文明?当人机共同进化协作,当机器成为一种“社会成员”,机器会有属于自己的文明么?这种文明是机器自动生成?还是依靠人类进行定义?
玛丽·米克尔的《2018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用户更愿意用隐私交换利益。“匿名用户”正在成为互联网的不受欢迎者,互联网欢迎的是把指纹、人脸甚至性爱体位偏好等隐私都交换出来的用户,比如“I Just Made Love”就是为全世界用户提供了性爱场所与体位的分享平台。此外,免费的有价值服务最终将成为历史,互联网正在因为甚嚣尘上的“社群”变得巴尔干化,在线社群日趋原子化一方面让个体获得所谓的“连接赋能”,而另一方面正在让互联网的连接价值被进一步削弱,比如各种微信群、知识付费社群的崛起。
当所有的人与设备都在线,连接成为一种生存意义本身,当物联网的无孔不入,让你在实施违法犯罪之前就可以将你进行了审判,当你的大脑被植入芯片,人的精神世界和意识都可以被任意读取和驯化,那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未来互联网》一书并非一部悲观主义著作,但我们不得不在眼花缭乱过度乐观的当下率先反思互联网的发展,当每个儿童一出生就像接种疫苗一样被植入芯片,人成为一种网络节点的数字原生代,人的价值与意义会是什么?我们健康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就是为了软件和芯片的正常运行么?我们的存在价值是为了让机器按照算法正常运转么?如果在线就是一种自由,一种参与未来互联网世界数字化分工的前提,那么离线和断网算不算一种刑罚或“数字监禁”?曾经寄予厚望的数字乌托邦会不会成为一种数字奴隶制?
彭博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当未来的机器替代人类劳动,下岗失业成为常态,作者建议成立一个财富基金,对机器劳动的剩余价值作为社会福利进行全社会分享。好吧,那欢迎进入以机器人作为劳动力的数字奴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