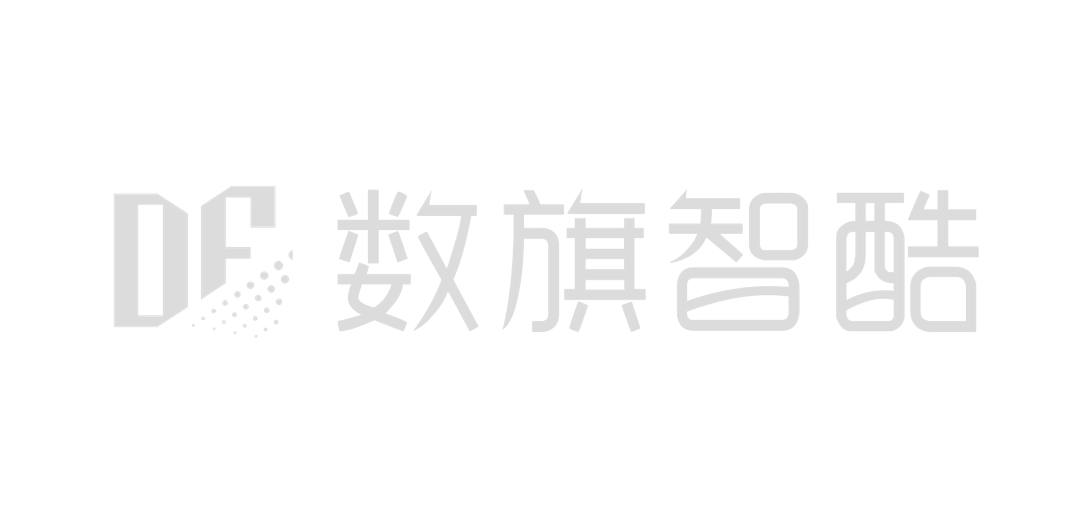从亨利·丘吉尔的“城市即人民”到腾讯研究院提出的“市民即用户”(“Wecity未来城市”观之一),表明栖居于数字时代的人不仅生活在城市中,同时生活在平台中、网络中、数字空间中,人不仅生活在客厅、办公室、餐厅、汽车,同时生活在微信、快手、淘宝、滴滴上。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后智慧城市”时代。
电子政务理事会副秘书长、数旗智酷创始人 唐 鹏丨作者
李 遇丨编辑
原告武汉智慧生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公司)诉被告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胜公司)、被告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软公司)、第三人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码公司)、第三人上海蓝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云公司)、第三人长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天公司)买卖及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武汉智慧生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暂时以败诉告终。据观察,行业关注的似乎并非谁胜诉谁败诉,而是“1.75 亿元智慧城市项目失败”让人触目惊心,华胜天成与微软作为被告,以及神州数码、蓝云网络、长天科技作为第三人,一时为行业所热议。
本文将不会对法律专业问题做探讨,也将排除与智慧城市本身无关问题的深究,仅从智慧城市的发展现状、模式、路径以及规律出发,尝试性地做出研究性评论,供方家批评指正!
为什么会失败?
“产城融合”的智慧城市乌托邦想象
武汉智慧生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诉华胜天成、微软等一案,暴露的是过去十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冰山一角,稍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一个关键词即是“产城融合”,在微软与业主方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中,微软公司武汉分公司落户开发区、智慧城市CityNext)项目合作、扶持新创企业、加入中国云体系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引入“微软IT学院”计划、授权合格教育机构建立“微软技术实践中心”等均寄托了业主方希望通过微软的品牌效应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愿望。
可以说,“产城融合”是城市乐此不疲地希望发展智慧城市的梦想,“引入一批企业,发展一片产业”是城市和新区的乌托邦想象,但现实比我们的想象要艰辛。以放管服改革、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契机,智慧城市的建设焦点正在从产业导向转向服务导向,此外,随着平台经济、产业互联网的崛起,我们可以看见,以IT集成商、基础设施服务商为代表的产业导向路径的智慧城市建设浪潮正在消退,而以平台企业、科技金融企业为代表的服务导向路径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浪潮正在兴起。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引入IT厂商及产业链企业进行的智慧城市建设,因缺乏“自循环”的利益内生机制而容易后劲不足,而通过引入平台企业、科技金融企业,因其具备强大的网络效应与生态辐射能力,比较容易与当地产业属性结合(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在电商、旅游、扶贫等方面均有相关案例),衍生新的模式和业态。
我们甚至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智慧城市的视域范围内,所谓“产城融合”往往是瓜熟蒂落的结果,而非事先人为设计的目的。对城市禀赋与平台经济的融合发展能力,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水平,最终就是“产城融合”的经济效应。
“产城融合”似乎是吊在所有城市额头前方一公里的胡萝卜,驱动它们积极投身智慧城市建设,无论是平安集团,还是华为的“城+市+产”,就算是谷歌也未能回避,就算是国外城市也未能免俗。谷歌的Sidewalk Labs在其发布的一份1500页的《多伦多的明天: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途径》的智慧城市总体规划中表示,希望为多伦多以及加拿大的经济繁荣带来希望。
传统的超级城市在寻找产业转型的出路,新开发的城市新区在寻找招商造城的机会,尤其是新城开发,它们都希望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与投资进行招商运作以实现导入产业的目的。在当下急剧变化的数字化转型关键期,拥抱智慧城市新空间思维(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融合对流),塑造数字经济新范式视野(引进和孵化一家代表性平台企业与数据服务企业),挖掘城市禀赋特性,着眼全球资源与资本,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与公共服务来筑巢引凤,这可能是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与技术周期下,每一个对智慧城市尚抱有“产城融合”期待的城市领导者需要考虑的。
失败的根源在哪?
数据运营缩短规划蓝图与市民体验之间的鸿沟
“智慧城市”存在于新闻报道、宣传片、研究报告、广告牌、会议展会中,这种现象曾经一直存在,直到互联网+政务服务、移动政务服务的发展才逐步得到改善:市民开始觉得“智慧城市”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系。智慧城市的市民参与感如何实现?应对考察团的智慧城市展厅实现不了参与感,用屏幕堆砌而来的指挥大厅也让市民无法准确感知,通过数据与平台建立市民生活细节与智慧城市发展的纽带,才是出路。
曾经有不少企业打出“智慧城市运营商”的旗号,但是要问的是:运营的一堆服务器、一个网站或APP,还是运营了市民的生活?由工程思维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最终的负责对象是招标方,而非市民,唯有产品思维与用户思维才可能使智慧城市由一个个项目成长为一条长长的赛道,可以不断跑下去,不断出现新的选手,新的风景。从交付即结束,到交付即是运营的起点,这是智慧城市项目需要转变的思路。
智慧城市规划设计存在两种极端,一是通过智库设计的方案由愿景主导,悬在云端,缺乏可操作的抓手;二是通过企业参与设计的方案由项目主导,以“接地气”的名气被商业利益所绑架。缺乏“上帝视野”,受困于专业门槛或短期利益所限,最终为城市设计的蓝图成为“难图”。
直白地说,我们还处于智慧城市的“蛮荒时代”,要么是过度看重硬件设施的建设,机房、摄像头、网络设备无所不用其极,要么是选择性忽视数据的隐私安全,缺乏一个隐私保护框架,从来没有去设想过一个人在数字空间“裸奔”的场景与后果。政务云、城市云的热潮,暂时性阻止和改变了“信息孤岛”、各自为政的趋势蔓延,但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云上的服务与应用创新生态构建。
数据运营要缩短规划蓝图与市民体验之间的鸿沟,首先是市民以何种方式与途径参与智慧城市规划,通过数据探针感知城市运行获取数据发现趋势是一种,通过泛在的平台入口收集市民意见是一种,通过VR、AR技术建模以提前让市民体验未来城市发展场景是一种……最难的且无法回避的是:当我们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告诉市民智慧城市的美好愿景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毫无保留地告知来自未来的风险?特别是当我们大多数人对新技术的理解还存在“无知状态”时,比如一个在城市生活的老人独自使用智能手机最后被广告“霸屏”到无法正常开机接听电话的恶劣局面。
如何规避智慧城市的失败?
实现从“城市即人民”到“市民即用户”的价值共识
无论是腾讯的“Wecity未来城市”,还是阿里的“城市大脑”,可能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放弃智慧城市包治百病的妄想,不要寄希望于一个通用解决方案去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而需要跳出2C的惯性思维,用2B的定制化解决思路去面对每个城市的独特问题。毕竟,每个城市都需要独自寻找智慧城市的出路。
对“智慧城市是什么”的这种终极追问,并未随着时间消散,谷歌的人行道实验室也在为如何定义人们心目中的智慧城市而焦虑。我们面对的是:大家都在埋怨智慧城市没有共识但又对推动共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美国原纽约市长、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著名城市规划师亨利·丘吉尔在其著作《城市即人民》里有一段话:只有在城市里,当思想的碰撞增加了才智,富余的财富催生了享乐,金钱的力量带来了安全感,才会出现进步和文明。我不妨在这里针对智慧城市仿写一段:在智慧城市里,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摩擦增加了城市韧性,用户认知的盈余催生了城市创新,数据的力量带来了安全感,也带来了焦虑,才会出现数据时代的“新城市文明”。
曾经我们以为PPP模式是智慧城市的建设运营的优选模式,然而个别地方的PPP“爆雷”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当PPP模式的最终目的不是与人有关的服务,而是成为一种金融工具,通过发布理财产品套利,那么社会风险就将向智慧城市的噱头聚集。目前我们看到,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度影响城市的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正在产生某种程度的互动效应,比如我们看到在国家行政学院发布的全国省级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排名靠前的省份和城市,大多拥有一个、几个甚至一批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企业,它们的创新能量在不断优化和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与社会治理能力。
从2006年的ebay退出中国,到2019年的Amazon退出中国,媒体统一归纳评价为:外国互联网企业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那么,从2009年IBM的“智慧地球”威胁国家信息安全,到2019年微软与武汉智慧生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官司,这意味着什么?我更愿意将之视为:数字基础设施的领导者迷失在数字空间主权世界的边境线上。苹果公司将中国用户的icloud数据存放于云上贵州就已说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在服务导向、用户优先的时代,经历过十亿级用户市场与长达20余年的产品训练与数据积累,腾讯、阿里这样的平台级公司显然更具备感知用户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粤省事、浙政钉等爆款应用进入政务领域。同时,这或许也正在宣告以IBM、微软等为代表的智慧城市“离线时代”的结束,以腾讯、阿里、谷歌等为代表的智慧城市的“在线时代”的来临,我称之为“后智慧城市”时代。
从亨利·丘吉尔的“城市即人民”到腾讯研究院提出的“市民即用户”(“Wecity未来城市”观之一),表明栖居于数字时代的人不仅生活在城市中,同时生活在平台中、网络中、数字空间中,人不仅生活在客厅、办公室、餐厅、汽车,同时生活在微信、快手、淘宝、滴滴上。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后智慧城市”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