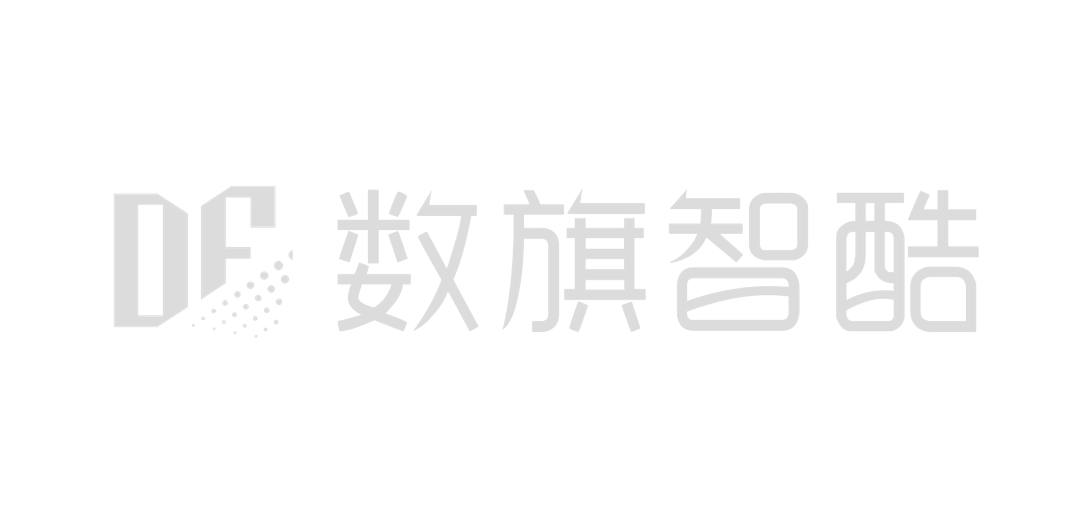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这是“韧性城市”首次出现在国家战略之中,也意味着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城市的不断“暂停”与“重启”之下,对未来城市发展方向与趋势的思考。
杰弗里·韦斯特在其著作《规模》一书中指出,一座城市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是两种流结合的产物,一种是维持并促进自身基础设施和居民发展的能源和资源流,另一种则是连接所有公众的社会网络中的信息流,两种“流”的作用不仅带来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社会活动、创新和经济产出的增长。这一点在数字时代的城市运行秩序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去想象一座城市被断电、断水或者被关掉WiFi网络,那将成为一座真正的孤岛。
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提出面向现代化的城市治理研究框架,其中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评估指标包括发展质效、精益治理、人本服务、多元协同四个模块,涉及城市环境、服务、安全、技术、数据、参与、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提出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愿景与探索性思考。在平台、数据、算法驱动的数字治理视野下,到底何谓城市治理现代化之路?核心在于如何建构城市的数字治理领导力体系,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指引下,建设性地平衡人与城、人与环境、政府与企业、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等利益与诉求,从谷歌旗下SideWalk实验室在多伦多滨水区智慧城市项目的搁浅,到丰田在富士山下“编织城市”的“数据合约”,其背后的左右发展结局的均是城市数字治理领导力的反映。
城市化进程“本质是政治问题”,因此,建构和提升城市数字治理领导力需要关注三个方向,其一是市民的“身份政治”。市民在城市中的权利与获得的服务,将不再仅仅依靠自我的社会身份,更依靠自己的网络身份、数字身份。使用什么品牌的手机与操作系统、下载与阅读什么样的APP、在什么样的平台拥有付费账号、跟哪位网红或大V具有社交连接……这不仅在构建数字时代原住民与边民的新“身份政治”,甚至正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之间衍生出鄙视链。
当市民都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一个数据感应点,坐上一辆网约车或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数据携带者”,那么,一个数据意义上的“新市民”就正在塑型完成——“新市民”的定义也必将从传统城市的一个空间迁移到另一个空间的户籍意义或是肉身迁徙上的“新”,发展成为从现实空间迁移到网络空间以及“虚拟即现实”的融合空间、从人到“比特人”及人与机器共同进化的“新”。
此外,“自动化推动生产到娱乐的社会转变”,当所有的生产活动逐步被关注用户体验的管理机制进行游戏化、娱乐化重新设计,——工作即游戏,游戏即工作。那么工作与生产的意义和价值也将被重新定义,对于城市而言,以生产效率、工业产值、就业岗位等为城市发展竞争力评价内核的考核标准将被改变,城市或将需要重新找到自身的发展使命。
其二是城市治理的“数据政治”。随着云计算、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传输速度、连接能力与调度能力逐渐提升与增强,人类将面临从“数字资源的云化”进化到“城市能源的云化”的“云端社会”。杰弗里·韦斯特在其著作《规模》中提到,“每套设备每台车辆乃至每栋建筑物都将具备输入和输出能源的能力。网络本身就能够通过与人类活动的互动实现削峰填谷的目标。”就像大数据专家涂子沛在其著作《数文明》中提出的“高清社会”一样——城市的每一个像素的动向都清晰可见,只是,未来将从对城市治理与服务对象的“高清化”,进入到城市资源调节配置能力的“高清化”。
对城市数据的运用直接影响城市的空间、行为以及竞争力,因交通失控而导致的道路瘫痪、因系统失控导致的大面积停电、因社交传播导致的骚乱与暴动……这些都是城市作为系统与市民的互动方式,表现出来的或正或负的社会影响就是基于数据的“数字生理反应”,而解决城市系统正常运行的能力考验城市的弹性与韧性。
此外,“社交化”正在成为城市治理与服务的重要趋势,社交平台与社交场景正在成为市民获取服务的重要平台和通道——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通信、交互与数据流,无论对于城市管理机构还是市民,不间断的数据流不仅仅是一种获得感的满足,更成为一种情感上的慰藉——一旦离线就可能显得焦躁不安。当一座现代城市决定切断通讯信号或社交媒体连接的时候,那一定是这座城市出现了不得不解决的艰难局面。这在马来西亚、伊朗以及中国的新疆都曾出现过。
除却“社交化”,更为引人注目的未来城市的“生物性”,依托于管理者意志的城市治理已经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城市的呼吸、节奏、频率都已被数字技术逐渐养成,尊重城市与技术双重规律是每一个未来城市管理者需要重视的。
其三是城市未来的“空间政治”。大量的网络协作工具、共享平台与资源的涌现,对市民的自主行动能力、创新能力及意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市的生产力也将变得“颗粒化”,而“自媒体”、“创客”、“一人公司”也正在大行其道,全球化协作成为潮流。
“信息时代三部曲”的作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曾提出过“流空间”的概念。物理空间不再是被认为是绝对的,它不能脱离数字维度而独立存在。当下的城市空间已经形成“数据对流”的形态,人在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中瞬时切换以完成服务动作,比如外卖、打车等等。假如一个地址在移动手机地图上没有被标注,那么我们已经几乎可以认为其不存在;假如一个城市没有在快手或抖音流行起来,那么它将丧失的即是向世界展示城市品牌的机会。这被称为“在线能见度”。
此外,不仅城市的市民被数字技术进行了能力解构与身份重建,城市空间也一样,从一种执行管理者意志的区域功能划分,转换为一种执行“数据流意志”的人本价值划分。在被数字技术不断赋能渗透的城市空间中,一些新物种在不断出现和进化,比如TED、一席、造就等国内外思想品牌,它们以开放场所为基础,通过现场与网络传播思想、标准、观点与生活方式,成为一颗颗寄居在不确定空间的城市“思想蚕蛹”,不断影响未来城市的文化取向。相对于来自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认知盈余对众创、众包模式的贡献,类似于TED的“思想蚕蛹”正以不露声色的方式影响一座城市的流行色。空间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符号,更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创新载体。
从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到深圳针对高校毕业生的“秒批”落户,再到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办事处招聘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毕业生……城市化发展到当下阶段,已不再只是批量吸收农民工以解决市政工程、楼房建设以及生活服务问题,城市开始有选择、有目标地对新市民、企业、产业等进行识别、过滤和筛选,通过政策工具进行城市发展策略与愿景的辅助和调节,只是在筛选手段和政策设计上的或软或硬而已,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开始离开一线城市流向三四线城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总部搬离一线城市,不断有新的商业物种或经济形态崛起在一二线城市之外。
因此,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之路,本质上是人与城市的适应性过程,在治理工具、手段与模式上体现的排斥或迎合,保守或冒险,最终都会体现在城市的新竞争力上,这一点在合肥、贵阳、东莞、厦门等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合肥在科技投资领域的“All in”、贵阳通过撬动全球资源发展大数据产业、东莞在智能手机之后向5G和AIOT转型、厦门开始瞄准新数字经济巨头总部……
城市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城市竞争力模型是什么?
依靠以经济发展体量、创新能力、专利数、产业政策、人才密度等传统城市竞争力评价已不足以概括和满足数字时代的城市发展诉求,需重点关注到的是城市治理的能力与绩效本身就成为了城市的竞争力内核。因此,未来城市的竞争力模型可以总结为“一性五度”,“一性”即城市的韧性,抵御风险、化解问题以及快速应变和稳定、恢复城市运行秩序的能力。“五度”则包括数据开放的“密度”,即城市是否具备源源不断的有效的数据开放能量,以释放城市发展潜力,并为创业创新创意构建参与城市未来的入口与生态;市民参与的“力度”,即城市政府是否具有更强的领导力与凝聚力,并通过便捷的数字化平台与创新机制体制,更广泛地汇聚市民的意见与建议,彰显市民作为城市治理主体之一的角色,以启发城市未来创新;数字服务的“温度”,即城市数字服务在信任、情感、交互等体验方面的设计逻辑,是否真正体现“城市即人”的温度,理解和尊重市民的服务要求与发展诉求;个人隐私的“尺度”,即城市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市民的私人信息和个人隐私问题,当遭遇非常情况时,城市政府及权力机关是否可能在做出行政损失与效率牺牲的情况下,以尊重市民的隐私,从而为个体在城市治理进步的过程中赢得尊严;城市创新的“浓度”,即未来的城市或将不再是以园区、孵化器、共享空间等方式进行,而可能深入渗透到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以及每一个城市场景中,“专门化”、被“划定”的创新空间将逐渐消失,公共化、泛在化以及社区化的创新空间和人群将不断涌现。
注:本文节选自《数字治理:中国城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