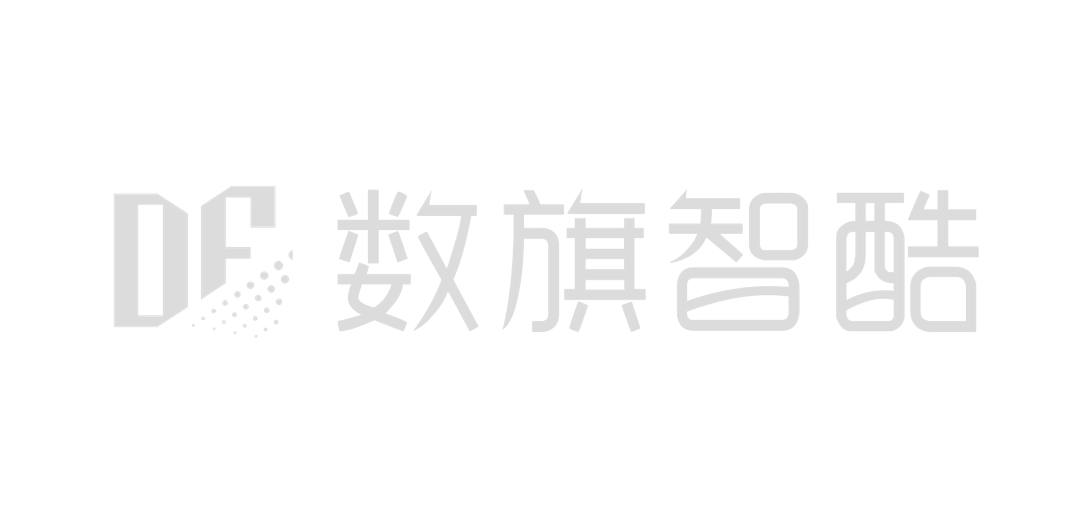数旗智酷关于2021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与十四五规划纲要系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此统一简称为“十四五规划纲要”。
作者 唐 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电子政务理事会副秘书长
来源 数旗智酷数字政府实验室
所谓“进”,指的是十四五时期的智慧城市建设在路径选择、价值逻辑与发力方向上,将全面、深度地与城市数字化转型融合互动,并逐步呈现出“数字赋能”城市运行的价值定位;所谓“退”,可以明显地看出,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极为克制”地对智慧城市的概念、外延及边界进行廓清,藉此希望推动智慧城市走出“特征包罗万象、本质含混不清”的学术聒噪与舆论阴影,并进一步界定了智慧城市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城市现代化的关系。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智慧城市”真正意义上出现过三次。在提升城市品质章节提出了“提升城市智慧化水平,推行城市楼宇、公共空间、地下管网等‘一张图’数字化管理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这里定义的“智慧城市”指的是通过“一张图”和“一张网”对城市地上地下空间、物件进行数字化管理以及城市运行的数字治理。此外,纲要提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开展以“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为核心特征的城市现代化试点示范。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我们终于认为,智慧城市或“智慧”作为某一种城市品质,是新型城市建设的特征和任务之一,但并非城市的终极目标与全部理想。这与之前见诸于专家演讲稿、PPT及相关地方文件的所谓“智慧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形态/新模式”是有相当差异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数据、平台、算法驱动的城市权力的剧烈博弈、技术与人文在城市服务和治理过程中所呈现的尚未被认同的价值选择与权衡、以及多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下的多元化需求的指向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回望全球智慧城市的发展态势,以纽约、巴黎、赫尔辛基等为代表的城市均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推动城市转型的通道与动力之一。面向十四五时期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或许我们可以更为坚定地认为:城市就是城市,所有的修饰都只是特征、意义与价值的最新发现,而非我们所要去向的未来城市本身。
针对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拓展城市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建立期限匹配、渠道多元、财务可持续的融资机制。从长远来看,从“数字化改革”到“智能化适老”,从新型基础设施到传统基础设施改造,未来城市建设的重要投入都将与数字化相关。如何创新投资建设运营模式,这是过去几年智慧城市建设无法绕过的话题。曾经一度被力捧为智慧城市建设运营经典模式的“PPP模式”,也因为其长周期运作模式及诸多不确定性导致的操作难度而并未被普及推广。本质上而言,PPP模式的特色与优势尚存在于传统城市建设框架内,与数字时代城市建设运营发展的要求仍有距离。就以高速公路与公共WiFi为例,高速公路可以通过企业投资建设并以收取高速费模式进行后向收费,但公共WiFi在数字时代却无法通过企业前期投资建设而后期以流量模式向市民收费。
随着科技公司在共享、出行、住宿、外卖等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庞大,除了政府采购、PPP模式,目前被不断延伸和复制的数字广东、城市大脑等模式是否会衍生出新的方式,值得继续观察。
在城市治理章节,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并特别提出了“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推动资源、管理、服务向街道社区下沉”。本次疫情在城市爆发过程中暴露的最大问题是,首先由于城市管理体系的层级互绕与条块纠缠,导致城市或超大城市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缺乏自主处置权力与流程,从而错失最佳应对时机。
约瑟夫·泰恩特在其著作《复杂社会的崩溃》中发问,大意是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发达的信息控制系统、任意使用的社会管控资源、大批专业的社会管理精英与技术官僚……为什么这样的社会还会崩溃,这是我还没有弄明白的地方。如果今天来理解这种“崩溃”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过于严密、规范、机械甚至刻板的流程和体系,导致整个系统规避了任何“失控”的可能,而恰恰是忽视了这种由于信息规则与数字空间领域“失控”机会的缺失,从而导致系统本身缺乏自我觉醒与自愈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防控局面基本稳定时北京、上海等城市就陆续明确和发布了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制度与豁免原则。
其次是城市基层社区在资源、流程、工具和体系上缺乏与城市运行中枢进行实时互动的能力,从而导致城市数字化能力无法直接赋能社区运行,只能成为指挥大厅与数据大屏供观赏的数字图表与看板,城市与社区疫情防控处于“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健康码”的出现其实是打破了原有城市数字化建设运营机制的一个偶然,但也是必然,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直存在的城市管理与社区管理的能力断层现象,有效地缝合、衔接和统一了城市治理从顶层到底层的“管理语言”。因此,当下提出的“智慧社区”、“未来社区”、“社区数字化转型”等,需要着重解决的是确保基层社区向上可以接受城市中枢的决策信号,向下可以输出社区居民的服务场景。这或许是“城市管理进社区”的必经之路。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建设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智慧城市”作为数字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过去几年我国在积极推进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评价,在强调与智慧城市的差异时以及评估方式,都将“市民体验”、“公众意见”作为考量。但本次提出的“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还是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传染基础设施改造为核心。
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在国家战略文件中同时出现尚属首次。大概在2013年左右,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汪向东先生就发表演讲指出“智慧城市、勿忘农村”,但这么多年过去,乡村的数字化除了体现在宽带网络、电商进村以及抖音快手的视频里,在整个建设质量上均不足以与智慧城市相匹配。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熊万胜在《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一文中指出,城乡社会”强调了中国的城乡关系内在的延续性:与欧洲社会“城乡分立”的传统不同,中国历史上每个完整的“地方”都有城有乡,并且城乡一直处在一种“粘连状态”。当代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城乡社会”体系,而并未进入一个纯粹的“城市中国”时代。虽然城市看似保持着对于乡村地区的强势,但它其实难以摆脱对乡村的依赖。这种独特的城乡粘连状态,与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相匹配,增强了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竞争形势的能力。
在这种“粘连”状态下,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模式、资源、路径等都相应受到影响,而最大的影响在于:我们永远不能假定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的群体和受众是一个标准的、完美的、一致的用户整体,而是大小老幼高低贫富等良莠不齐错落分布的集体。这也决定了我们的管理模式与服务体验模式需要更为精细化地设计与应对。这也是复杂社会的一部分。
肉眼可见的趋势是,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或“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主题将演化到“智慧城市如何与数字乡村融合”,当智慧城市的目标真正回归人与城市,当数字乡村的语境从“扶贫”转移到“振兴”,政府、企业、公众及社会组织如何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愿景下突出自身的主体意识?还是拭目以待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