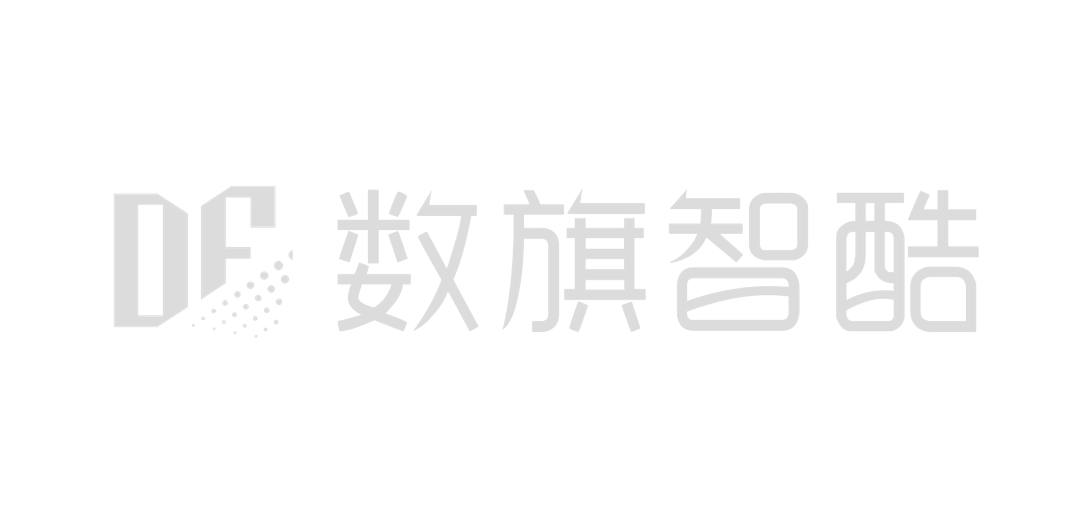本文为《信息助推,或适得其反:为什么知道的并非越多越好?》一书的书评文章

我至今记得在2015年第一次翻开卡斯·R·桑斯坦的《简化:政府的未来》的那个下午,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撬动了我对数字化、政府、治理、用户体验、信息行为等不同论题之间的关联性思考,也是促使我对“互联网+政务”研究兴趣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读到《简化》,才有了我与其他研究者合著的第一本书《互联网+政务:从施政工具到治理赋能》的诞生。2015年是桑斯坦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的第四年,但我认为他几乎在《简化》中预言了后十年的数字政府发展走向。
桑斯坦在《简化:政府的未来》一书中延续了之前他与人合著的畅销书《助推》中的观点,即当人们在冗长的信息或复杂选项中做出决定时,自主选择的结果往往是很随意的。因此,需要通过分类、简化以及优化决策链路,以不同的选择架构会吸引不同主体的注意力,从而让大脑做出不同的判断。
《信息助推,或适得其反:为什么知道的并非越多越好?》一书可以看做是对《助推》的进一步延续,作者针对信息决策、信息行为以及信息从决策磁场进入到社会舆论、群体情绪、公共空间中所导致和演化出来的各种冲突与结果,进而说明:信息的价值、意义与效应是在具体的时间、空间中被人的个体认知、群体意识以及潜在观念所干扰与决定的。信息披露的主体的诚意、决心以及初衷,并不能决定信息为社会和公众带来好或坏的后果,尤其对于政府而言。
“信息平权”、“信息对称”、“信息平等”等词汇的背后,似乎都在表明:只有当我得到的信息与你得到的信息一样多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权利、地位、收益就将是平等的。真的是这样吗?“知道的太多对你没有好处”,这似乎一句威权主义、官僚主义以及犬儒主义杂糅语境下的忠实告诫。但是,桑斯坦通过诸多案例研究毫无褒贬的告诉人们:你知道的信息并非越多越好,有时会适得其反。
信息公开具有折射效应。当一根筷子插入水中,我看到筷子在水中的位置与这跟筷子真正处于的位置是有距离偏差的。信息也是如此,没有信息不是处于不同群体的误解与错觉中,所以才有非理性的现象出现。比如食品监管部门要求对转基因产品的信息披露,目的是为了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但对于用户而言,潜意识会将自己的杂食信息、道听途说等与权威公示进行混合学习使用,然后得出“转基因=有毒”的自我暗示。而只有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信息判断力的少数公众才能对信息做出理性决策。
信息不是中性的,它携带了披露主体的权力意志与价值取向。比如当政府机构在特殊时段要求对牛奶、棉花、海鲜等产地国家进行公示,一旦与公共舆论、国际关系、民粹主义浪潮被混合理解,那么,沉默的舆论海面就可能掀起滔天巨浪,它会有意识地暗示和助推人们对某一种信念的支持,以及对某一种群体的反抗。而带来的可能是社会的混乱、市场的非理性失调,对经济运行正常秩序也会产生不良后果。
信息披露并不是越多越好,它是在现实与历史、事实与想象、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社会价值与个体感受之间进行的一种平衡术。
《后资本主义的生活》的作者吉尔德曾经写过《知识与权力》,在那本书中他提出,“只有令人惊奇的事物才有资格被称作‘信息’”。而在信息披露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消费过程中的行为而言,最好不要太多这样的“惊奇”。比如,如果在IBM的主机上标明:这是一台由一家曾经为纳粹生产过“打孔机”的公司生产的服务器。比如,如果在一台iPhone上标明:这是一台由非洲矿场、富士康工厂的工人以伤害自我健康的方式进行制造和组装的智能手机。这样的信息是事实么?是。但这样的信息披露对谁有益处呢?除了降低销量,进而会损伤品牌和剥夺工人的劳动权利,其他毫无用处。
又如,我们在公共厕所就可以发现,小便池上方的提示”向前一步靠,滴水不外落“,这样无足轻重的告诫往往对人没有丝毫情绪上的刺激,而当你发现上方的提示是“尿不进去,说明你短”的时候,这种性别尊严的信息会让你重新考量自己的行为,虽然没人在旁边监督。这样的信息是事实么?并不是。但这样的信息对促进公共卫生有价值么?当然有。那么这样具有广泛共识且没有实现难度的卫生常识,为什么在几乎所有公共卫生间均无法践行呢?“人们通常想做的是那些别人实际在做的事,而不是别人仅仅认为应该做的事。”这或许是我们在所有信息决策中所面临的社会境况——嘴上说不要,但身体很诚实。
对于信息而言,“知道”的反义词并不是“不知道”,而是“不理解”或者从自身利益立场出发的“选择性理解”。作者在本书中举出了香烟健康警示的案例。比如通过文字提示“吸烟有害健康”可能并不能对消费者产生足够震慑的警示作用。那么通过图案呢?比如国外香烟盒上将发黑的肺部、烂掉的牙齿等作为警示图案,希望以此吓退一部分消费者。但可能产生的是两种结果:一部分消费的确知难而退,另一部分消费者可能会直接忽视图案——通过自我屏蔽信息来满足抽烟的心理愉悦。
如果从信息披露对象所产生的反应来看,在中国的地铁上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案例。地铁上的爱心座椅是为老幼病残孕留出的专座,这体现了地铁运营方的道德关怀与服务伦理。从健康人的角度而言,这种信息的披露本质是在激发一种美德,而对老幼病残孕的当事人而言,这种信息就可能存在一种道德凝视,甚至于一种具有“凌辱性”的公共检视。所以你就会经常看到或听到这样的事件和新闻:当你想给一位儿童或老人让座的时候,对方总是推托拒绝,他们认为自己不属于“老幼病残孕”的行列,当你向一位腹部隆起的女士让座的时候,她会很尴尬地拒绝,因为她只是有些胖,并没有怀孕。
除了信息对不同对象可能产生不同的心理暗示,对不同背景的人群也有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比如我们习惯性的阅读是从左至右,但是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则习惯从右向左阅读,所以我们的信息披露主体按照大众习惯进行公示信息的时候,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与其他人对信息的接受能力与效率将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助推”之后,作者提出了“恶性助推”的概念,即在“助推”过程中由于信息披露产生的摩擦、坎坷与沟壑,从而导致最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本应该得到帮助的人被技术性忽略。比如低保、残疾、跨性别人士等可能因为生理性原因或者隐私因素而拒绝自身的信息披露,而他们面对的公共部门在确认其身份、资格和条件的时候又必须知晓这些信息,这种不对等的供需状态将直接影响服务的质量。这可能也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进一步推动技术实现个性化解决方案的问题。
从作者对信息价值的意蕴理解而言,当前,特别是在信息过载的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对信息的满足感和愉悦,并非来自人们从信息中获益,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占有欲,就像我们刷朋友圈和短视频一样,当信息极大的丰沛充斥着人们的大脑,人们的麻醉可以忘记痛苦、烦恼和一切危险的临近。人们在被信息流俘虏的同时,反而感觉自己掌控了信息。这真是一种奇绝的心理效应。
我们不能忽视信息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的出现往往由于一些行政程序或官僚机制上的推动。比如,出于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要求,不同数字平台都推出了隐私保护政策,但是从来没有几个人去阅读这些文档。对于平台而言,隐私保护政策的目的并非为了“保护隐私”,而是以一种强迫性的、惯例化的操作手段,让用户以百无聊赖的方式在肯定他们应对隐私保护的工作成效的同时,默许放弃自己的隐私。比如,出于廉洁自律的要求,有些医院会要求医生签写廉洁自律声明,承诺不收受患者红包,医院也会出台规定要求医药代表不允许进入诊室。但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更具有信息的比较优势,这将不可避免地让患者与医药代表对以上信息进行有机可乘、有利可图的反向理解。
作者感叹,“出于道德动机的披露仅仅是表达性的,产生一种感觉,即某些事情已经完成的错觉,但实际上并没有帮助到任何人”。如果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告示、标语等作为案例来审视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无数个辛勤的工作人员在背后付出的努力,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价值。
作者认为,只有将信息披露前后的社会影响、福利效应、道德后果等进行较为深刻的多方利弊权衡,最终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信息决策与选择。以我国的政府决策行为为例,比如北京周边某市推出“买房落户”政策,瞬间引发京津冀经济圈的需求人群蜂拥而至,政府的初衷是以天津的城市优势加上落户政策来消除房屋库存刺激市场,但由于政策引发大规模的需求集聚,不仅导致政务服务压力剧增,同时也因为房产和户口价值稀缺性的降低从而相对意义上偏离了政策执行的预期绩效。
此外,以教培行业的双减政策为例,初衷是为了规范课外补习的行业乱象,但政策出台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行业上市公司和从业人员,此外并未严格意义上杜绝课外补习,反而导致行业由地上转入地下,变相“补习”以不同面目出现。如果从桑斯坦的视角出发,双减政策的确导致了相关上市公司的创富能力断崖式下降,致使行业从业者大批量失业和转行,但是从整体社会效益的政策成本与收益角度来看,双减政策是否会真正降低家长的教育成本、心理焦虑以及对人口生育信心的激励?这二者之间是否可以进行货币化计算,以验证政策本身的影响程度?
作者在“估计 Facebook 的价值”一章中写道,人们只愿付出平均7.38美元来使用 Facebook,但需要得到平均74.99美元才愿意放弃使用 Facebook。在停用一个月后,在另一个月停用 Facebook 的用户要求得到的中位数金额是87美元,按照 Facebook 在美国的1.72亿用户计算,如果每个月每个用户获得了87美元的福利,每年的总金额将达到数千亿美金。也就是说,社交媒体容易让人产生“政治性抑郁”与相对性痛苦,但用户宁愿放弃87美元的福利也要继续使用 Facebook:花钱让自己变得痛苦。为什么人们会要求一大笔钱来放弃一个似乎让他们不那么开心的平台?当媒体和专家不断告诉我们:社交媒体让人产生焦虑、负面情绪以及生理紊乱,似乎社交媒体只有这一种信息价值。而不可忽视的是,我们似乎对社交媒体上维系的朋友关系、亲戚联络以及技能学习、社区认同等视为一种不易觉察的信息,过度被情绪信息刺激而掩盖了信息的正向工具价值。
如果以近期发生的农夫山泉事件为例,我们就会发现,当下互联网的舆论空间已不只是“极化”、“信息茧房”、“回音壁”那么简单,一位备受尊重的企业家故去引发的不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共鸣,而是导致了对同城另一位企业家的攻讦与构陷,似乎一位企业家的伟大必须以另一位企业家的阴影进行衬托。素人亲自下场以“传说”、“神话”、“野史”的方式进行罗织素材和论据制造,以支撑自身的论点,从而不负众望地赢得支持者的持续追随,掌声和喝彩声越热烈,离最初的讨论主题就偏离得越远越离谱。
农夫山泉事件告诉我们,一旦嗜血的 Nobody 们无意中触到了网络情绪的开关密码,那么“信息披露越来越多”只是一种错觉,信息被“假性再生产”才是真相——看似信息被证实,其实是用一个谎言论证明一个谎言。它们通过“扯淡”——跟事实的真假无关,就是为了将话题继续下去——的方式,以情绪拉扯与认知屏蔽来推动公众阐释的再造,从而实现它们自身也不知道自己要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和实现什么的目的。每一个人都在“信息纸房子”的构建中获得一种满足感,但这种纸房子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但讽刺和悲哀的是,这种“信息纸房子”的兴风作浪与看似固若金汤,只是因为可以反驳它们的人都不屑于与它们争论。
《信息助推》一书揭示了信息决策的复杂性。如果从数字政府角度而言,我只想说,这些年我们对数字化的企图与要求太高,对政府决策本身的完整度、完美性以及科学性有不切实际与不着边际的幻想,而忘记了:公共决策的质量并不由决策者的智慧或决策过程民主与否决定,而是处在由“公共”的时间、空间、状态和行为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它不仅与决策信息的拟定、发布与推进流程有关,它还与信息触达的主体、场域以及当时当地的场景与氛围有关,这一切都会影响公共决策的信任与绩效。
那么,让我们重新回到该书的中文版标题:《信息助推,或适得其反:为什么知道的并非越多越好?》,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当国家机器对社会运行的干预能力与理由越来越强大和充足,当数据与算法裹挟的政府权力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处置越来越模糊与不透明,一个强政府会多么希望听到这句话:你们知道的越多对你们越没有好处!这会是桑斯坦所预料到的所谓“听到错误的东西”么?这是作者可以提前预知的“信息暗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