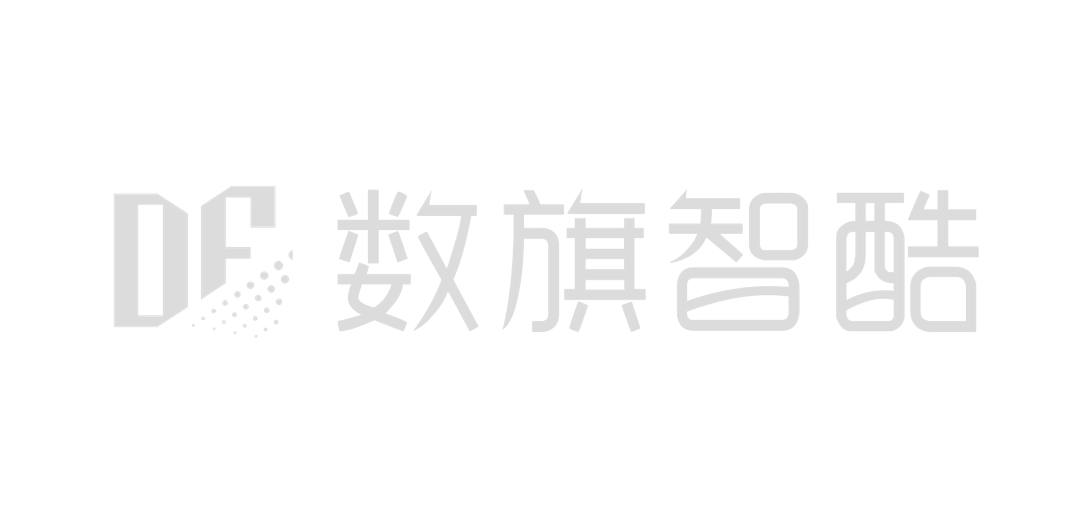本文为《A City Is Not a Computer》的书评

2023年5月,在《纽约客》刊发的一篇题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漫长余波》的文章中,作者写道:古典自由主义作为一场运动,它已经破产;作为一种信条,它依然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智慧城市作为一场运动早已结束,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将长期存在。
如果让我推荐四本关于智慧城市的书籍,我会首推威廉·J·米歇尔的《比特城市:未来生活志》(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这部出版于1996年的著作以极具预言气质的写作风格,亦真亦幻地对当下的智慧城市建设做出深刻的洞察。第二本是麻省理工大学可感知实验室的卡洛·拉蒂与马修·克劳德尔合著的《智能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作者提出了”城市即数据流“的概念,并对智能技术如何影响城市治理提出了前瞻的设想。第三本是由波士顿城市数据科学家本·格林撰写的《足够智慧的城市》(The Smart Enough City),作者从自身实践出发对未来城市如何认知、融合和驾驭恰当技术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最后一本应该就是《城市不是计算机》(A city is not a computer),作者Shannon Mattern(香农·马特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以过去15年从事档案馆、图书馆、人类学以及媒介研究出发,阐述了技术和数据驱动的城市“隐喻”的可疑与破产,并展望了未来城市逃离技术陷阱的方法。这本书是由作者于2017年发表的《城市不是计算机》一文扩展而来。
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智慧城市不仅包含了技术至上主义者的狂热,也隐含了技术虚无主义者的无奈。不仅被矫饰为官僚系统在决策失误、治理失范之后转移视线与减缓疼痛的完美借口,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在舆论喧嚣中失去对未来的基本判断后自觉形成的一种单极化审美的群体共识。树木、人体、平台、大脑、智能体、操作系统……都是过去这些年我们对智慧城市赋予的隐喻,隐喻的背后则暗含了我们对智慧城市一种修辞上的理解极限。我们希望将数字化冲击下的“城市”这种复杂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融合体框进我们由自私、贪婪、势利、恐惧、狂热等包裹的意识形态。当我们试图通过隐喻来接近“城市”的真相时,而事实是我们离“城市”的本质越来越远。每一种隐喻都隐藏了一种个体的偏见或群体的欲望。
香农·马特恩通过《城市不是计算机》告诉我们:将数据时代的城市形容为“平台”、“大脑”、“操作系统”、“智能体”等昭示了人类企图用数据驱动建立“服从性秩序”的野心与被算法简化和肢解大脑思维结构后的浅薄。数据智能只是智能的一种形式之一,而智慧城市的“智慧”长期以来受到了数据与算法的单一化调教与驯化。现在我们需要利用来自浩瀚的自然、社会、历史、经验等多种本土智慧的“嫁接”,以让城市摆脱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叙事,重新进入可以带领人们驶向未来的轨道。
从“仪表盘”到“驾驶舱”:作为一种城市隐喻的破产
与智慧城市作为一种产业技术浪潮裹挟而来的舶来品不同,“城市大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词汇,曾被誉为可以媲美伦敦的地铁、巴黎的下水道与纽约的电网一样伟大的发明。这毫不奇怪,在高速推进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字化浪潮中,每个稍微有点想法的人在巨大的舆论与话语冲击面前,都会自觉地产生一种参与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心理暗示。也正是这种“心理暗示”,最终汇成了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幻象》一书中提出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提到城市大脑,当然无法不提及“驾驶舱”,很显然,这是一个让任何拥有控制欲的人都无法拒绝其魅力的词语。
只是当我们迷恋“数据大屏”或“数字驾驶舱”的视觉冲击时,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一下其祖宗——仪表盘。“仪表盘”这个术语最早诞生于1846年,原意是指车辆前部的挡泥板,防止马蹄和车轮溅的泥水弄脏车辆内部。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直到1990年,这个词的涵义才成为“屏幕提供了各种信息的图形摘要,通常用于对某项业务的概述”。也就是说,“仪表盘”实质为一种保持整洁和秩序感的必要而存在,那些在真实世界发生的污泥、脏水以及沿途踩踏过的花草,都可能因为仪表盘的存在而错过。究其原因,仪表盘的存在并非为了反映真实世界,而是为了在真实世界之间建立一道让人可以接受甚至倍感舒适的屏障——它既抵挡了我们对未知的焦虑,也阻止了我们随时可能暴露无遗的无知。因此,香农·马特恩指出,“仪表盘的设计者有一个‘炼金术的野心’:他们寻求通过神圣的方式变出一个崭新的现实。仪表盘的制作者意图不仅仅是显示系统的信息,而是生成分析人员可以用来改变系统的见解,使其更有效或更安全。”
为决策者提供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与掌控力,这可能就是“数字驾驶舱”设计者引以为豪的价值所在。
在作者眼中,今天的城市仪表盘、数字驾驶舱、城市大脑等都正在变为一种城市治理的“护身符”,上面沾满了不同的决策者与建设者所写下的“咒语”,充满了保护城市的力量。只是,数字时代的护身符不是以戴在手上的戒指或挂在胸前的玉佩形式出现,而是以发光的屏幕形式出现。当我们的智慧城市建设者将那些闪闪发光的数据大屏部署在市政建筑物、参观大厅以及运营中心,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聚集数据占卜未来和塑造政策和做法,使理想的世界成为现实”。如此看来,那些数据大屏前面的人来人往,与前往寺庙烧香的香客和信众并无二致。“这些护身符本身也有固有的风险:咒语不起作用的风险,护身符没有被正确地‘净化’或‘充电’的风险,所希望的未来不会实现的风险。”
人类试图通过数据来反映和操控现实的历史并不久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鼎鼎有名的商业巨子,还是被历史选中的政客,一旦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某种可以释放权力控制欲的技术,他们的“宏伟愿景”就油然而生,阿里的马先生表示“大数据可以实现计划经济”,京东的刘先生认为“我们这一代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无疑是智慧城市主义的忠实拥趸。香农·马特恩认为“我们应该拒绝将关键的、通常是道德决策委托给机器的数据驱动模型”的时候,而我们似乎认为将关键的社会发展决策委托给机器的数据驱动模型是一种人类驱使机器的荣幸、一种人类驾驭自然规律的重大成功。
我们如今都知道“智慧城市”是源自2009年IBM“智慧地球”的商业宣传,而事实是智慧城市主义思潮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创立了社会主义政党的智利总统阿连德在1970年代打造了“Opsroom”——“城市大脑”的雏形。在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领导下,智利试图实施Cybersyn项目(赛博协同工程),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用于管理国家经济的决策支持系统。一个呈六边形的Opsroom是它的智能管理中心,领导者可以访问数据,做出决策,并通过电子化传输将信息传递给公司和金融机构。Opsroom的六面墙壁中有四面可供放置仪表盘,管理员可以使用椅子扶手上的按钮控制台来控制显示哪些数据可以展示——如生产能力图表、经济图表、工厂照片等。

1970年代,智利的Opsroom
伊登·梅迪纳(Eden Medina)在《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一书中解释道,阿连德主导的赛博协同工程是一种旨在摆脱美国等强国的“技术殖民主义”的明确尝试,作者认为,“这种殖民主义迫使智利人使用适合富裕国家需求和资源的技术,同时阻止替代的、本地形式的知识和物质生活的繁荣。”反之则意味着将本地知识与价值观念纳入就可以摆脱技术殖民主义的束缚。这一观念似乎与《城市不是计算机》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用一种外向型技术来寻求一种满足内向型需求的合理性。
Cybersyn并没有帮助阿连德将智利经济摆脱技术殖民主义的阴影走向想象中的繁荣,在美苏争霸的生存缝隙里,他最终扛起了卡斯特罗送给他的AK-47来面对国内叛军的炮火。从1970到2023,智慧城市在全球政府与城市竞争的倚重程度和政策关注度也可以看出:智慧城市虽然脱胎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但它的“精神父亲”显然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计划控制的国家意志。
当然,并非中国的城市管理者痴迷于“数据大屏”和“数字驾驶舱”,欧美国家的城市管理者也不例外。1999年,巴尔的摩市长马丁·奥马利,面对严重的犯罪率和高税收设计了Citistat,其中一个使用需求就是在政府内部建立其问责流程。据内部表示“可问责性”的修辞在仪表盘发展的整个历史中一直很流行。如果将“可问责性”进行中国化,那就是“数据留痕”、“可追溯性”。几年后,市政府翻新了CitiStat Room,各部门的领导们站在一个讲台上,面对着一面墙的屏幕,为他们单位的业绩负责。看出来什么没有?所谓仪表盘或数字驾驶舱,它之所存在的根源是——通过基于数据的高效问责机制来维持官僚系统的顺利运转。它所强调的高效并非治理本身的高效,而是追究责任的高效。
从仪表盘发源于马车挡泥板的历史也可以看出:仪表盘的核心不在于“展示”,而在于“屏蔽”——屏蔽所有不适合量化、不适合可视化展示以及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信息。
自1908年开始,仪表盘逐渐从一个测量电流、速度以及燃油量的表盘,进化成为一个包含发动机温度报警系统,越来越多的指示灯开始出现。“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械操作被自动化,仪表盘进化为象征性地而不是索引式地传递它们的功能。”也就是说,功能和数据的增加并没有提升对汽车状态的准确性,而是越来越模糊、越无法准确获取汽车的真实状况。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却无法做出准确决策的原因——因为当部门或机构在将数据量作为一种工作成绩进行炫耀的时候,他在试图告诉你——他所展示的数据和屏幕本身如何漂亮,而非通过数据来实现决策支撑的成效。
当仪表盘本身的设计和建造成为一种越老越考究的工作时,仪表盘的存在价值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仪表盘的设计开始不再由汽车功能、驾驶需求来决定,而很大程度上由美学来决定。仪表盘成为一种心理安慰剂,它提供一堆毫无用处的数据信息,让驾驶员以为自己在控制一个强大的机器,其实“大多数‘关键性能指标’与司机和汽车性能之间没有多大关系”。仪表盘已经成为一种作秀的工具,就像当下电动汽车的中控屏一样,它逐渐培育了驾驶员的身份和结构——因为要读懂和使用这种中控屏也需要语言、界面美学方面的新素养。仪表盘成为一种象征形式。
作者更是鲜明地指出,被设计师、规划师、工程师、投资者、技术人员、开发商和企业家城市领导人多年来一直支持的“嵌入式传感器、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无线信号,联网的智能手机、仪表盘和无所不知的操作系统将产生前所未有的效率、无缝连接和便利”的未来城市愿景,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但是,实现这些愿景的技术手段却被不同的企业和政府所利用。原因在于,智能技术往往可以提供更为便捷的权宜解决方案,“它们提供了一种快速的、往往是有利可图的、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免除了领导者调查和解决卫生与种族不公正以及系统崩溃根源的责任”。智能技术已成为一种卸责与掩饰不作为的工具。
弗雷德里克·泰希曼在1942年的飞机设计手册中写道:“所有的控制系统都终止于驾驶舱;所有的操作和导航仪器都位于驾驶舱;所有关于飞行的决定都来自驾驶舱。”
那么,请问当下每一个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的设计者,每一个拍板上马智慧城市运行指挥中心的决策者,我们的城市治理决策是否/敢于适用于以上三条标准呢?如果不能适用,那么我们设计的意义又何在呢?
从“平台”到“操作系统”:数据主义支配的城市假设
互联网的连接性让人们重新想象城市的可能性,而将城市比喻为一个平台或操作系统曾被视为一种兼有数字哲学与网络魅力的绝妙隐喻。Platform(平台)一词源于法语plateforme,最早出现于1540年代,解释为“行动计划,方案,设计”,到1550年代,被称为“地面平面图,绘画,草图”。虽然现在这些意义早已过时,但在被智能化叙事影响下的“平台”一词又同时展现了其包容性与局限性。作为一个被硅谷科技企业家塑造的词汇,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与盈利性解决方案,“平台”的面目越来越复杂。知识产权媒体学者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就指出,科技世界中“平台”一词的弹性特征——它既具有结构性、计算性和政治性,又意味着开放性、中立性和平等性,这使得它很容易销售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承诺的所有东西,并充满了创建者的偏见。
大概十年前,新的隐喻将“数据库”称为平台,指的是开发人员创建新的应用程序、技术和流程的基础。作者认为,现在“平台”的隐喻开始以“平台式城市主义”的形式转移到城市,并以“平台资本主义”的形式迁移到经济学中。当我们将“平台”视为一种多边交易、交流和交互的数字经济生态基础设施的时候,当投资人和创业者宣称“我们需要确定做‘平台’还是做产品”的时候,当普通消费者逐渐将“平台”亲昵地称呼为“万能的××”的时候,当我们认为“平台”的平等、中立、自由、公平等在为每个草根赋能的时候,其实平台的“幻觉”正在被逐步唤醒。
作者认为,所谓“平台”不过是一个二维的资源陈列柜,用户参与平台的过程往往被眼花缭乱的肤浅表面所吸引和沉溺,从而缺乏对其结构、逻辑以及背面的思考和批判自觉。“我们只看屏幕上的真相,而不检查产生真相的数据、算法、代码和电缆。正是这种不加批判的思维助长了错误信息的传播、社会弊病的技术修复、计算模型的盲目崇拜以及将强大的仪表盘视为认识论的神化。”因此作者建议,“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在制度或技术平台上形成的‘混乱而丰富的人际和思想网络’,而且需要关注网络的煽动性。”
当然,无论是“平台”还是“操作系统”,这些修辞均源于“城市是计算机”这一假设。程序员和技术作家保罗·麦克费德里斯解释了这种想法:“城市是一台计算机,街景是界面,你是光标,你的智能手机是输入设备。这是一个基于用户的、自下而上版本的城市计算机的想法。但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版本,这是基于系统的,它着眼于城市系统,如交通、垃圾和水,并想知道如果这些系统是‘智能’的,城市是否会更有效率和更好的组织。”
香农·马特恩认为,“城市是计算机”的假设,“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图形或地面、结构或基础设施、界面或代码上”。这些隐喻也暗示了规划者、管理者和市民对城市建设的不同位置或程度的潜在干预,信息在城市系统中的流动方式,以及什么样的市民数据是可操作的或“可执行的”,甚至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底层价值逻辑,“城市是计算机”已经将人的因素排除在视野之外,需要的只是点击、移动、复制、打开、放大、删除以及关机、重启。如果对照中国在疫情期间与疫情后的社会恢复情况,你就会发现:“城市按下‘暂停键’”这一表述显得多么狂妄而肤浅。
在作者眼中,类似于Sidewalk的多伦多智慧城市项目、沙特阿拉伯的The Line以及丰田的Woven city,似乎都是一种智慧城市技术主义的狂想,“是城市规划师、技术专家、科幻作家和电影制作人就开始设想体现计算或网络形式的网络城市和电子乌托邦”,洋溢的尽是技术原教旨主义者对人类文明的蔑视与不屑。智慧城市的隐喻正在不断被更新,比如从“智能体”进化到“生命体”。而就我看来,这种更新不过是对“智慧城市缺乏人文主义”批评的一种略显委屈的迎合,而从来也根本不会转变智慧城市作为一个数据与算法产物的叙事基因。
作者认为,“城市是计算机”的思想谱系可以追潮到二战后诞生的控制论,由于受到计算和军国主义模式的启发,城市科学家将城市设想为一个信息或视觉系统,而城市规划则是一门沟通、信息和控制的科学。对城市化的控制论设计视角是当代呼吁城市从互联网上崛起的明显前兆。“城市是计算机”的理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将城市生活的“混乱”定义为可编程的,并服从于理性秩序。用“量化有序”数据来控制“感性无序”的城市,没有比这个更让人感到一种具有征服意味的成就感了。人类学家汉娜·诺克斯认为,“作为社会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与通往现代解放政治的道路,信息和通信技术体现了秩序战胜混乱的希望……”或许“城市仪表盘”、“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等都成为将这种“希望”塑造为“现实”的载体。
对秩序感的渴望导致彻底的无序,对混乱的治理导致的愈加混乱,这似乎成为人类通过数字技术介入城市治理欲罢不能的方式,就像赌徒一样,总希望用自己手中的技术作为筹码能为眼前的无力感扳回一局。
《城市发展史》的作者刘易斯·芒福德曾将城市描述为一个信息丰富的交流空间。作者认为,如果刘易斯·芒福德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拒绝将一座城市视为一台计算机或互联网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他会提醒我们,城市建设的过程比编写数字空间优化的参数要复杂得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被注入历史的偶然性。城市不是计算机,但在面对复杂化、高风险的社会治理现实面前,我们的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一次次地希望将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以及城市安全问题简化为算法。
在城市的逻辑中,“偶然”是一种不间断的日常,而在计算机的编程逻辑中,“偶然”即是Bug,是事故,是系统必须排除的不稳定因素。城市规划是一种理性行动,但它的目标却是为城市生活的感性建立一种必须遵从的秩序。
所谓将“可计算”、“可识别”、“可寻址”等视为智慧城市的运行特征,所谓“我们可以数清楚一个城市有多少台汽车”,所谓“我们要摸清楚一个城市的数据资源底数”,其实都是“城市是计算机”的典型写照。他们不承认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且信心百倍地以为自己依靠技术能为城市创造一种新的规律。因此,在一个缺乏宽容而又不容许“模糊”的城市治理价值观指导下,所谓“弹性治理”、“韧性治理”可能都是某种被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一厢情愿在膨胀。
所以,当我们接受“城市是计算机”、“城市是互联网”的理念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幻觉之外的平台隐含的教唆、煽动以及剥削。而当平台就像城市交通一样掌握了“流量分发”、“限流”、“封号”等治理技术时,我认为这并非抑制了平台“弗兰西斯坦化”的前兆,而更可能让自私、欲望、极端主义等加速滋生与蔓延。
智慧城市只有“更新”,没有“维修”
智慧城市主义的意识形态告诉我们,每一次宕机、升级或重启都代表着一次“更新”,而不是“维修”。我们擅长用“更新”来创造一种永远向前、永不止步的假象,从而掩盖了一些千疮百孔、无以为继的事实。“维修”是一个工业时代的词汇,而“更新”则代表了一种超然“修补”之上的“创造感”。而从城市政府的视角而言,他们用“城市更新”来取代“拆迁”,“更新”有一种暗含的对美好生活的未来承诺,而“拆迁”则意味着一种破坏、剥夺、损毁以及对历史的否定。
如果说“利维坦”是工业时代精英阶层对国家机器的象征,那么“弗兰肯斯坦”可能就是智能时代草根群体对技术与权力合谋感同身受的普遍日常。智能技术与国家机器的结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庞大的虚无”——我们无法描述其规模,也无法抵抗其力量,我们有的只是如影随形的恐惧。而“更新”似乎成为延迟这种恐惧的缓释剂——我们总将希望寄托在下一次“更新”。
作者认为,当电视机这样的家电设备需要维修的时候,家庭主妇必须邀请电视修理工上门服务,维修的场景本身成为了一个半公共化的社交场合,而女性消费者则“以自己的方式接触电视中更复杂的方面”。而随着家庭领域将更多的智能技术引入,如平板屏幕、传感器和语音助手,这种半公共化的接触机会越来越少,大家都开始上搜索引擎、直播间进行自我学习。当智能技术降临的时候,我们的电脑、汽车、智能摄像头等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远程维修和启动的,而这些机器的算法、操作策略等很大程度上是无法“修复”的。
如果“维修”创造了某种工业时代的社会性景观,那么“更新”则导致这种基于智能设备的“半公共化场合”的隐匿。
智慧城市主义笼罩下的生活工具和运作方式的改变,不仅改变了个体生活,而且改变了社会结构。智慧城市的一切在表面上维护都是自动化的,如果没有维护人员的话,大多数软件应用程序、平台和门户都会很快崩溃。但真相是,我们可以维修硬件,却只能“更新”软件,但“更新”的潜台词是:万物可变,算法不变。
《巴黎:现代的城市发明》一书写道,1662年,当由皇家颁发的专利特许牌照的私人投资商将公共马车在巴黎投入运营时,不仅带来了城市没有私人马车的底层人士与有私人马车的贵族在城市流动中的流动公平。由于等待马车过程中的推推搡搡、穿越陌生人拥挤的过程,这在历史上第一次推动了不同阶层的人在同一个空间里近距离相遇。而如今呢?当电视机维修店、裁缝店、钟表维修店逐渐消失或隐匿在平台的数字地图上,那些真正促进城市公共交流与阶层融合的机会在逐步丧失,那些跨阶层流露人类良善与温暖的空间和机会在减少。因为“更新”是不需要现场进行的,“更新”与时间有关,与空间无关。
如果从作者的视角来看,当前对智慧城市的“更新”或“维护”定义都过于单一,需要围绕个人、社区、城市、生态的责任和义务来进行定义。“如果我们希望更好地支持世界上的维护者所执行的关键工作,我们必须认识到维护包含了一个标准、工具、实践和智慧的世界。有时它使用机器学习,有时则使用拖把。”
或者更进一步说,所谓智慧城市的“维护”,有时是技术上的,有时是制度上的。但目前我们过于简单地将智慧城市的“维护”定义为一种“技术补丁”的更新工作。
公共图书馆是智慧城市的“避难所”么?
可能由于作者从事人类学、图书馆相关研究的原因,香农·马特恩似乎认为公共图书馆是可以用来打破智慧城市现行叙事的重要杠杆。公共图书馆作为一座保存城市记忆、静态知识、生活经验、历史民俗的场所,与智慧城市的快速变化似乎形成了对冲,以低熵对冲高熵,以静止对抗流动,以中立对抗偏见,以平和对抗激进……
现在应该没人认为“Google是一个免费图书馆”了吧?从“不作恶”到“做正确的事”的价值观转变,从创始人布林狂妄而无知地宣称“如果世界各国的军队都与谷歌这样的国际组织合作,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国防承包商合作,对和平更有好处”,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相比于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知识的象征”,平台创始人偏见的渗入,让它已不仅仅是“煽动”,或正在成为暴力的来源。当人工智能崛起的时候,将互联网作为一种免费共享的“知识的象征”就显得更为可疑。《经济学人》就曾报道,俄乌战争期间,乌克兰海关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行了一批制作炸弹的化学品配方,而入境之后落入到民间,平民可以通过ChatGPT来学习自制炸弹。而平民的参与正在颠覆战争伦理。
作者认为,在一个以公共知识为中心的社会,图书馆可以发挥重要的、革命性的作用,作为数字避难所,认识论的过滤器,隐私培训师,公民数据的仓库,以及开放获取材料和公共技术的宝库。作者希望将图书馆定位为“智能城市主义的逻辑和政治中的一个潜在的关键代理人,以及一个避难所”。也就是说,智慧城市主义造成的割裂、偏见和对抗,希望公共图书馆来进行愈合、抚慰以及缓释。用知识的不可量化、不可预测以及情境化,来抵御智慧城市主义的可量化、控制性以及编程化的僵硬与独断。
在信息噪音充斥的网络空间,每一个“消费”信息的人都需要一套成熟的价值框架,才不会被算法所左右,成为“主动择食”而非“被动喂养”的数字动物。而图书管理员很少会将图书、信息作为一种商品,他们不需要“转发”、“点赞”,他们的借阅数据也不需要通过仪表盘或驾驶舱来显示,他们不需要标榜什么,也不需要通过数据来判断什么或主张什么。
作者认为,图书馆管理员长期以来接受了关键的信息素养培训,包括检查图书信息资源,以更好地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呈现和价值所在,以及了解如何建立图书馆本身的政治历史、分类系统、体制结构等。因此,与Facebook、Google相比,情报学者萨夫亚·诺布尔(Safva Noble)认为,这些商业平台对公共领域是有害的,不仅因为它们助长阴谋论、暴力以及错误信息的传播,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缺乏有意义的多样性,不成比例地依赖于不稳定的劳动力。这一点似乎在《比特暴君:硅谷政治经济学》和《幕后之人》这两本书中都有极为深刻而露骨的阐述:缺乏女性、少数性别群体参与平台的决策而让平台走向过度“男权化”的倾向;内容审核、数据标记等工作对发展中国家低端廉价劳动力的运用以减少平台的运营合规成本。
正因为如此,香农·马特恩认为,“仅仅改革我们的系统是不明智的,让平台企业改变他们的商业行为,期望他们像公共利益信息领域或门户一样运作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初衷。我们需要的是向公民提供更多的投资,来帮助我们了解平台的运作逻辑”。这或许就是《技术陷阱》一书所提倡的方式:通过社会福利、教育以及薪酬改革,来建立人们对抗和逃离技术陷阱的能力,而不要渴望平台会迎来顿悟时刻。有所不同的是,或许作者没有看到或想到,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过去的十年,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公共服务支撑与供给中却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用户教育、服务体验等方面的创新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当“数字鸿沟”在表达人与人之间因数字化发展造成的阶层权利与能力沟壑的时候,“技术陷阱”在暗示人们的技术权利获得与使用的差距来自于政府权力是否积极作为。
公共图书馆究竟能够为打破智慧城市主义的魔咒创造何种可能性?或者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全社会建立对城市技术的客观看法提供批判性的意见与视角。
作者认为,数据与算法驱动的城市充满了监视、追踪、评分、分类,并不公平地实施奖惩。而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发展“有用的”、生产性的知识,使自己能够批判地、有意识地生活在自动化的数字系统中,同时也为缓慢而低效的想法,为“意外的、不相关的、奇怪的和无法解释的情形留下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行使作为市民的监督责任,比如当摄像头正在盯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盯着所有监视摄像头和传感技术,对决定哪些身体部分会上传到云端的算法进行逆向工程,质疑限制谁能获得知识的技术协议和法律政策。
在智能技术的“风车”面前,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唐吉坷德。可笑的是,我们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机就是自备的“鼓风机”。
城市的丰富性被平台简化为一个直播间、一条短视频或一篇10万+,那些被数据和流量滚动伪饰为一种“常态”的信息,在真实的世界中可能是极为稀少的个案。“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保护读者隐私的机构,以及一个日益接受数字正义原则的机构,图书馆可以而且必须将自己定位为剥削性数字城市主义的‘例外空间’”。或者说,香农·马特恩想象中的公共图书馆在智慧城市中的价值角色即是一种“技术之上主义的抗体”。
智慧城市不仅仅是消费通过平台获取和提供给我们数据,它还将深层次和分布式的基础设施和人类智力作为塑造我们知识体系的基础,并“指导和规划”我们的价值观。作者认为,与其去建立一个机构或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来对抗这种由风险资本和狂人制造的技术利维坦,不如回到城市公共空间,通过公共利益技术系统和社会契约相互促进,促进更加包容和公正的认识论和伦理价值观:一个利用其基础设施来关心维护和构建丰富多样的公共知识的图书馆,是这些知识定义了我们的城市。
但现实是什么呢?如果作者来中国走一走或许就会明白,从“淄博烧烤”、“曹县棺材”到“贵州村超”,网红直播间里的流量正在定义一座城市的精神和品牌。那些由短视与逐利心态造就的政策行动,不是对智慧城市主义的拒绝与担忧,而是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迎合与追随。他们不关心传承,也不在乎历史,他们迷信城市需要依靠一两个机会或者一两个风口来“崛起”,而不是细水长流的长期主义。
在《城市不是计算机》这本书的最后,作者似乎表达了她对智慧城市应该包括一个公共图书馆的愿景与诉求:
如果Western Yard建成,我希望它能包含一个公共图书馆,在那里,顾客可以学会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数据使用,创建他们自己的数据集,用于优化以外的目的,开发技术来抵制监视,讨论建立数字公平和数据正义的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那里,他们可以辨认出无数种智能的形式——工程学、兽文化、鸟类学、海洋科学、海员、工人、隧道建设者和在此之前曾居住过这一地区的莱内普人的历史知识——这些都嵌入在他们所站立的平台之下,隐藏在平台背后。
很显然,作者对公共图书馆在智慧城市进程中的价值寄予厚望。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将人们从智慧城市的教唆与驯化中抽离并逐步形成批判性思维的空间。世界上的智能有无数种,而数据智能只是很新且并不如想象得那么高深的一种。如果城市作为平台、作为计算机,它背后的基础设施需要被重建。
公共图书馆真的可以成为拯救智慧城市的“避难所”么?我觉得未必,一个城市的阅读人口,一个对城市技术具有批判能力的开放式决策机制,一个对世界的变化抱有慷慨、宽容、勇敢与成熟心智的市民群体……或者才是智慧城市的观念基础设施。
“嫁接”:一种打破“智能螺旋”的设想
大数据的出现让人们内心逐渐生成一种“洞察未知、计算未来”的野心,而对于非结构化数据、弱关联信息的整合分析,也代表了一种“野性”联系在四处萌芽——毫不相干的弱关系事件可能会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关系”结果。
作者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观点认为“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构建了有害的社会条件,从根本上塑造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平等”。他的理由有四:一是与新冠病毒相互作用的多种疾病,影响了不良的健康结果;二是穷人、有色人种的多种风险因素,以及种族居住隔离、无家可归者和医疗偏见,最终会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三是获取医疗知识以及医疗资源的渠道,决定了疾病的最终风险与后果;四是在流行范围内的医疗体系复制了历史上的不平等模式。在一个社会认知、行政伦理以及舆论基础都呈现固有缺憾与偏见的土壤之上,同样的疾病将遭遇截然不同的结果,从而丧失掉基本的个体权利。
为了矫正这种不平等现象,作者又以“以解决不均匀遮阴问题的系统性修复策略”为例,来证明综合性、系统性解决措施对解决复杂城市问题的可借鉴意义。比如将洛杉矶街道改善与全面的遮阳计划相结合,通过扩宽人行道、将电线埋在地下、开挖更大的树坑、种植多叶抗旱的树木,为拱廊、画廊和公交车站腾出空间。从而这样将城市能源、交通、可访问性和公共健康的治理之间建立关联。让市民开始认识到城市绿化景观不只是景观,它与能源、知识、服务以及健康密切相关。
假若这种美妙的城市治理图景能成为现实,那么它所遭遇的门槛和障碍是什么呢?如果反观中国的话,我劝大家最好去了解一下一个街边餐饮店安装一个煤气罐需要涉及多少个部门,而不是去指责某个店的安全意识缺乏或者某个部门没有尽责。
从工业时代的背影里走出来,我们迷信“没有量化就没有管理”。香农·马特恩认为,城市智能的很多形式都不适合于数据化或“商业化”,如舞蹈、仪式、食物、运动和口头文化等城市知识是不能被简化为“信息”,也不能被静态展示、储存或通过光纤电缆进行传输的,它们是重要的城市智慧——生活在每一个市民的身体、思想和社区中。这些知识比作为平台所能表现的可量化的城市数据更为稳固和持久。显然,作者认为不可简化和量化的“信息”是推动一座城市在幽暗的历史中不断前行的重要力量。
作者认为,那是由于我们那些带有偏见的价值观、不公正的服务理念以及陈旧的恶习正在逐步嵌入到我们使用的每一项新技术,从监控设备、搜索算法、图像识别等等,从而导致像算法、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工具并非建立一种倡导公平包容的社会伦理基础之上,而是嫁接到了“腐烂的树根”上。这应该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新兴技术的应用越深入而城市治理却变得越来越糟糕的原因。
如何解决这种来自“底层价值”紊乱导致的结果呢?作者在书中做出假设: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社会和认知基础设施嫁接到技术和建筑基础设施上,并重视公共设计、拥有权以及对这些系统的维护。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培育了优先考虑环境、种族和数字公正,从认知多元性中吸取营养,将计算逻辑与野生智慧、感官体验和本地知识相结合的城市根基。一座建立在识别其树木、雕像、界面、档案、边缘社区和更多超出人类蕴含的智慧的城市,最终比任何超级计算机都要智慧得多。
用多元价值理念“嫁接”来解决智慧城市主义的技术极化问题,这看似一种理想主义解决方案,但似乎又是一种隐喻的升级——它暗示了一种通过多种价值认知元素的中和可以稀释被沉淀的观念浓度、降低毒性,以及为城市发展注入健康与活力来达到修改城市运行底层“源代码”的可能。读到这里,我感觉作者又重新进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她或许认为:将城市不可数据化的知识进行数据化之后,就代表着一种新的价值认知的融合与诞生!?但事实是,在将何种非数据的知识进行数据化以及在数据化之后并入到系统处理的时候,也是存在选择和决策过程的,在这种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中,新的偏见将不可避免地诞生。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嫁接”来展现智慧城市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丰富性,但是,谁能确保不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呢?曾经我们不是将互联网称为“网络共和国”、“数字乌托邦”么?结果现在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试图通过网友“举报”、“指控”等公众力量的参与来阻止故意诽谤和造谣对企业正常运营的影响,而这样的机制设计却被某些企业所利用,它们的公关人员一旦发现有媒体或信息平台发布任何他们不爽的内容就可以发起举报,从而导致媒体变得“噤若寒蝉”而不知道该写什么,最后的结局是企业可以传达给市场的信息越来越不透明,能够发布的可能就只有产品广告信息了。
因此,在一个崇尚集体主义审美与国家主义美学的社会,在一个人人惧怕犯错且时刻警惕被冒犯的社会,智慧城市在底层逻辑层面的丰富性与多元化该如何建造呢?
我不知道。谁知道呢?Ta知道呢?
最后,我认为,《城市不是计算机》的价值并非对正在流行的智慧城市意识形态提出犀利且深刻的反抗,而是在被“加州意识形态”长期支配的智慧城市领域,当所有的男性管理者、创始人、女性高管以及女性研究者都在为技术沙文主义的成就击节赞叹的时候,作者香农·马特恩带着温和、宽容、坚韧以及建设性的嗓音勇敢地发出了女性主义的声音,尽管他所提出的解决思路尚需要时间去验证。但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城市研究史上必须拥有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