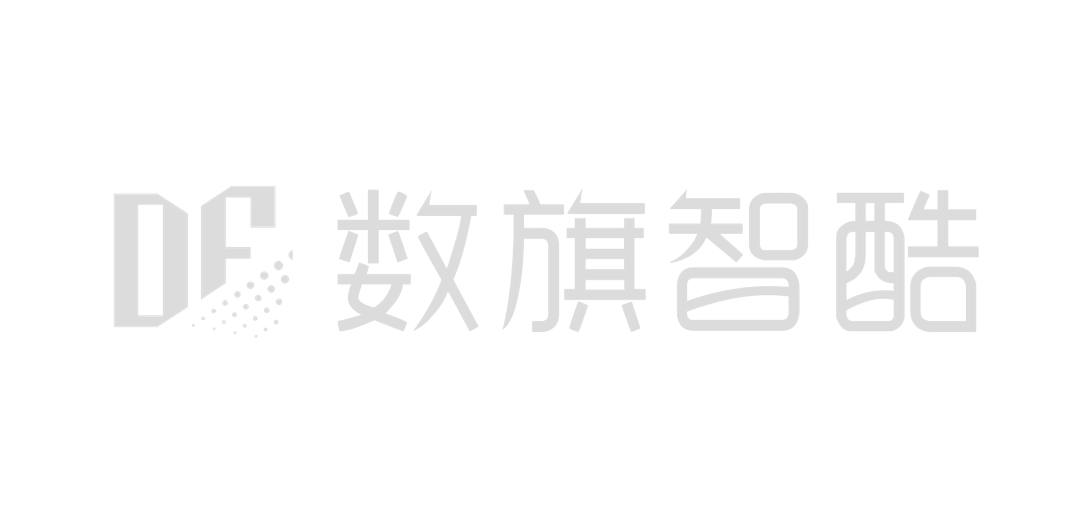本文为《Recoding America》的书评

奥巴马或许不会想到,倾注了他的政治理想、致力于提供全民医保的《平价医疗方案》,最大的阻力和障碍并不是在签署之前共和党人的极度抵制,而是在他正式签署后通过 HealthCare.gov 提供在线医保服务,才是他“好心办坏事”的黑暗时刻的开始——HealthCare.gov甫一上线就因为数百万人注册而不堪重负崩溃,以至于第一天只为八个人成功地提供了服务。“致力于公平的努力但没有产生公平的结果”。
詹妮弗·帕尔卡 (Jennifer Pahlka) 是奥巴马政府的 CTO 副手,就在她上任三个月时的2013年10月,HealthCare.gov 正式上线,然而该网站的表现让她近距离地看到了“备受赞誉的数字政务服务的失败”。作为 Code for America 的创始人,詹妮弗·帕尔卡出版了自己的新书《Recoding America:Why Government Is Failing in the Digital Age and How We Can Do Better》(重新编码美国:政府为何在数字时代失败以及我们如何做得更好),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自身的项目经历、案例复盘以及近距离观察,给出了她对“我们的数字政府何以走到今天”的看法。
如果要高度概括《重新编码美国》这本书,以及回答“为何失败”的核心问题,我想至少有三个答案:一是最初的技术体系已无法满足今天的服务要求;陈旧的代码、破烂的架构以及积重难返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技术补丁,这让每一次数字政府的升级都增加了不关乎进步的辎重与累赘;二是底层的法律系统其实早已为当下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从美国1946年的《行政程序法案》到1965年的《布鲁克斯法案》,其实早已从行政系统的运行弊端与政府参与技术项目的边界提供了线索,所以后续的一切看似或恢弘或渺小的失败,都只是现行法律体系下的注脚;三是官僚系统的运行设计与积弊已经和数字时代的运行需求相去甚远;为工业时代的“效率”与“管理”而建造的、从“司法国家”跨入“行政国家”的行政系统,我们仍然残留了“审判人民”而非“服务人民”的积习。所以,“我们申请政府服务的人感觉政务服务平台就像一个宗教裁判所”。
对于中国数字政府的研究者或从业者而言,《重新编码美国》能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认为,它至少告诉了我们:全世界的政府官僚系统面对数字时代的高速发展,它们都葆有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本色,比如无视公众需求、缓慢而迟钝的反应、偏爱追求规模效应、天生保守而追求“无罪”的流程、如无要求则不越雷池半步的职业精神……
《重新编码美国》似乎告诉我们:在数字化呼啸而过的时代面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官僚系统的应对策略和姿势并无二致。而更糟糕的是,詹妮弗·帕尔卡认为,“现实情况是,在我们今天的体系中,民选领导人几乎没有动力去建设二十一世纪的国家能力,政治家不会因为简化和合理化管理服务提供的庞大法律、政策和法规而再次当选。” 你看,资本主义体制的政府也在担心“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问题。而如果再看看中国近十年的数字政府发展,是不是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简政放权”动力往往来自于自我定义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使命,而资本主义多党制政府的服务承诺与改革行动则是以兑现选票和支持率为准则。作者认为,对于政府而言,每一个失败的数字系统背后,不只是一次预算支出的浪费,其实都包含了权力争斗、部门利益纠葛、领导力问题以及组织内部的价值观冲突。
防御型制度文化诞生不了人性化服务
“当崇高的目标通过复杂层次结构层叠时,它们会变得难以辨认”,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政府与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当政府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其公共服务目标的时候,它不得不通过在线平台来触达用户和输出服务。而数字服务的本质是由一个一个界面和一个一个超链接构成,“超链接”的涵义本身就是层次复杂的多层结构组合,是为了方便从A链接到E的代码解决方案,但中间的B、C、D其实没有被完全省略,对于政府服务而言,它需要被行政系统的事务性工作去消解。因此,当一项政务服务涉及到的部门越多、节点越庞杂,那么它所要通过的审批、许可等就越多,最后,那些初始的崇高目标当然会难以辨认。比如当一位美国退伍军人申请医保服务的时候,复杂和繁冗的程序让他有一种屈辱之感。而这种屈辱之感应该同样存在于中国的大型城市积分落户申请场景中。
防御型制度文化首要考虑的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失误而被起诉或质询。而至于用户的办事体验,那是最不重要的。如果要真正改变这种糟糕的体验来为用户着想,他们考虑的不是所谓的“自我革命”。从詹妮弗·帕尔卡的自身亲历来讲,她曾因为一次办事经历而被工作人员“邀请”去起诉他们,对方的逻辑是:只要你发起了起诉,我们才可以改变,才可以推动流程优化。否则,我们永远都会做“正确的事情”。
如果要问,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考核、各种各样的绩效评估,那么,这种防御型的制度文化的生存土壤是什么呢?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所谓的政务服务能力与水平的评价只是自欺欺人的伪命题。我们推出的标准、规范、准则等,并没有衡量政务服务的质量,而是衡量政务服务机构的行政工作表现,是衡量他们是否积极配合评估以及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和数据。政务服务质量与政务服务机构的工作表现是两码事。但是现实是,我们非常乐意地混为一谈。
因为防御型制度文化的目标与数字政务服务的目标、路径都不一致,由此带来的结果即是: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限制政府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而事实往往适得其反。“健康码”算不算一个典型案例呢?那些因为办事需求而无节制要求公众重复提交材料的政务服务算不算呢?所有这些其实都为了实现一种政府行政程序的“合法性”,为了维护和保全这种合法性,我们行政事务上的巨大努力和投入精力,远远大于我们在服务设计的投入和效益。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政策、文书和流程的黑洞里消耗。最终反馈的社会影响是什么?就是“数字形式主义”。
经常有人会说“政务服务需要懂业务的人”,需要“老法师”,但是谁说“懂业务的人”、“老法师”就能提供高质量的政务服务体验呢?“懂业务”与“做服务”这中间没有任何必然性的联系。也就是说,“对法律和政策的精准、繁琐的解读与理解,对创造一项可交付的服务体验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懂业务”的“业务”仍然是政务服务工作范畴内要求的“业务”,并不是老百姓的心声与痛处。
詹妮弗·帕尔卡在《重新编码美国》这本书里提到一个笑话:
一个人坐在热气球上飘上了天空,他着急地找到一个地上的人。
问:你能告诉我现在在哪里么?
答:你现在离地面30公尺,北纬40°-42°,西经88°-90°。
问:你是工程师吗?
答:我是。你怎么知道?
回:因为你说的这些对我毫无用处。
想想我们所遭遇过的那些糟糕的、无聊的、啼笑皆非的政务服务体验,他们多么像这个笑话里的工程师——准确而毫无用处。
我们看到大大小小、高高低低、起起落落的数字政府建设浪潮中,真正伤害公众的反倒不是原有的官僚主义弊病,而是因为数字化推行过程中青黄不接、无所依靠、仓皇失措的政务服务现实。比如以前的“不见面审批”,现在又推出视频式的“边聊边办”,下一步准备干什么?可以说,每一次治疗其实都在产生一次新的创伤。
数字政府为什么应该从“小项目”开始
詹妮弗·帕尔卡建议政府停止向外包大型项目投入资金,转而关注小规模可交付成果:“就像风投资助初创公司一样,他们得到少量资金来学习、适应,然后在获得成功后获得更多资金牵引力。”由于其规模可控,这些项目能够优先考虑用户的需求并做出调整以推进政府政策的成果。用风投思维来推动数字治理产品的建设和发展,这当然是一种创新。但是,我觉得至少目前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在中国。存在的一个很浅层次的逻辑就是:小项目无法进入大领导的法眼,继而得不到更大的支持和关注,最后的命运就是自生自灭。如果稍有一点成绩,在向上汇报的材料中也会被纳入到某大型项目的成绩,而这又将对团队的信心造成打击。
所谓“大项目‘有病’,小项目‘有用’”。基于数字平台建设的所有政府应用,都必须在行政程序和法律体系中找到平衡,不仅需要考虑内容生成、规模效应、用户思维、涌现逻辑等,还需要考虑作为公共服务应用的法律合规、道德伦理以及公平普惠等,通过“小项目”来冷启动一项服务,然后通过A/B测试来完成用户体验测试与用户教育,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逐步“增加功能”,而不是增加操作界面。“健康码”、“救命文档”、“口罩预约”等其背后都符合“小项目”的逻辑。
“大项目”最大的问题在于,几十家公司几百上千人同时驻场开发半年的政务服务应用,可能面面俱到满足了决策者心血来潮的所有需求,最后在用户面前成为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然后望而却步的“怪物”。所以作者认为,“从更简单的技术系统与应用入手,最后可以交付更大的系统和应用”。“小红书”最开始是一个类似《精品购物指南》的PDF电子文档,而支付宝最开始是需要手动记账计算的。
但是,为什么在数字政府领域“大项目”如此受欢迎?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数字政府的建设逻辑似乎也脱胎于传统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铁路、高架桥等建设逻辑,他们或许认为:主要打通了大动脉,毛细血管就会自然畅通,建设好高速公路之后再铺上农村的水泥路才有价值。而事实是,数字化项目的建设逻辑恰恰相反,它必须让用户一点点地逐步适应和认同,继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使用与参与,最终小溪潺潺汇成江河的滔滔不绝。
政治学者刘瑜认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现在看来,政务则是一种“确定性的艺术”,它需要通过提供稳定、恰当、可信赖的服务,从而建立起政府信任。从云计算到生成式AI,科技变化太快了,从全球各地政府的政策、法律和项目立项来看,政府一直在希望跟上技术的步伐。而真相是什么?“政府需要跟上的不是技术,而是人。科技导致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而无法对我们保持宽容”。科技无法宽容我们,则需要我们自己设计可以宽容人的技术,或者叫“科技向善”。
作者认为,数字时代的政府需要与公众建立一种“共同语言”。何为共同语言?既不是技术语言,也不是法律语言,而是人的内心所想,即用户心声。而通常情况下,这种用户心声并不会直白而显性地裸露在外,需要真正为民着想的政府去观察、探索、发现和满足。
“政府永远做不好技术”是另一种迷信
“政府永远做不好技术”,这句话有两层意思,政府会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制定和执行政策,技术的问题交给企业和社会去解决。企业会认为政府的行政系统比不上企业运营的效率,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用户负责,此外公共部门的薪水太低招不到优秀人才,所以当然做不好技术。结果就是对外包技术公司的极度依赖,从依赖技术开发、依赖项目申报立项到最后绑定整个系统的行政秩序与服务质量。
帕尔卡在书中提出一个经典的问题:当企业家们说“政府永远做不好技术”,因为低工资得不到最好的人才,那就只得问一问:他们所说的“最好”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介绍一个人是一个很棒的程序员,我们第一时间会想“他来自哪里”?我们的脑海里浮现的通常是:脸书、谷歌、微软、亚马逊……或者腾讯、阿里、百度,我们肯定不会想他是在一个地方城市的政务服务平台开发了“健康码”、“惠民保”、“食品券”、“口罩服务”等应用的人,因为互联网裹挟的财富、资源、等级认证等建立的“人才叙事”告诉我们:人才已经被大公司垄断,“好的人才”就是“年薪高的人”。“好的人才”需要获得更好的尊重,奥巴马在给一众硅谷科技大佬开会的时候专门为 healthcare.gov 的一位普通技术人员的出席而等待,这似乎就是在向硅谷示意:政府也可以做好技术。
“最好的人才”是拥有优秀高超的代码能力还是拥有对公共利益关切的责任心?如果他们没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意识与情怀,代码的产出速度和编程技巧再高,对我们的数字政府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作者认为,“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以及思考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伤害的意愿,是任何领域的资产”。我们的数字政府建设外包企业有谁思考过“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伤害”吗?
当 Uber、Airbnb 等共享经济企业迅速崛起,资本主义的激烈市场竞争为普通大众带来便利,而在公共服务这样一个“厌恶竞争”的领域,资本主义的精神仿佛顿时失效了,丧失了一切被资本主义被证明过的优点,具备了一切官僚系统的缺陷。就算甲骨文、亚马逊、微软、谷歌这样的公司加入到数字政府建设阵营,我们又看到了什么改变呢?“以科技解决政策上的困难”是甲骨文等这类公司的陈词滥调,也是他们赚钱的方式。但是这并非事实。事实是科技并没有真切地解决政策的困难,相反的是,需要政策的创新来解决科技赋能公共服务的“困难”。
英国 GDS(政府数字服务)的同行曾对作者说:如果精英不能像理解经济、意识形态或宣传那样理解技术,你就不能真正正确地管理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如何依靠一个完完全全由外包技术公司建立的系统和平台来管理一个城市或国家呢?
作者认为,外包技术厂商在政策制定者和使用数字服务的人们之间造成了“令人衰弱的距离”。对外包供应商代码的依赖也可能导致无法提供关键的公共服务。比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西雅图会按常规给患者做流感拭子测试,但是当疫情已经开始社区传播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反应过来需要做核酸测试。是他们不愿做、不知道怎么做、没有能力做么?都不是。只是因为在系统程序的流程上,核酸测试的数据需要增加一行命令而已。
再比如疫情时期的失业救助金申请,我们可以看到杭州、深圳等地推出了“民生直达”在线申请发放补贴。而美国在公众申请失业救助金的时候,会需要回答“过去半年是否因为工伤请假或旷工”时,如果回答“是”,这个用户的申请就将被审查,而无法继续申请。这是一个日常申请的流程,并不适合疫情时期的用户场景。这只需要修改一行代码。但是,由于这个流程陷阱的存在,造成了在线的申请疯狂积压。
数字政府的真正悖论
据统计,目前每个美国人每年需要42小时来处理政府服务的相关文件,全年所有美国人将有10.5亿小时消耗在政府的行政系统里。此外,美国人每年需要花费60亿小时收集数据和填写纳税表格、100亿美元做税务准备,以及20亿美元投入税务准备软件。没有人统计过中国人每年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来处理自己的政务服务相关文件,以及收集数据和填写表格的时间。也许在“数据多跑路、群众多跑腿”、“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的支持下会有所提升和改善,但那些隐性的时间成本仍然是无法忽略的。
作者指出:“我们拥有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两个最糟糕的东西:惩罚人们的自动程序与漫长而繁琐的服务流程。当我们致力于改革前者的时候。为什么不追求简化后者呢?”为什么呢?因为官僚机制的潜规则告诉我们,在“开新局”和“补旧锅”之间,我们会永远选择前者。或者说,致力于在数字世界的改革,或许也是我们逃避现实制度改革的方式。毕竟,用数字化的方式,将行政流程的痛苦转嫁给公众,总比完全由自身承受要轻松一点。
卡斯·桑斯坦是奥巴马首届政府白宫信息和监察事务办公室主任,他在《简化:政府的未来》(2015)一书中指出——
我们不能忽视每年去除几千万小时的文书工作的要求,也不能忽略推进直白语言的使用、废除过时的规定、提升公众参与度、使用合理的默认规定、强行要求实施执行纲要,以及推出采购前直白明了、完整的顾客须知规定来取代原先复杂难懂的信息须知。在多个领域里,我们取缔了无用的样板文章。单击一下就能搞定的政府工作模式还没有出现,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里,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
从2015年到2023年,时隔八年,中国与美国似乎都在“政务服务白话文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用直白明了、完整的顾客须知来取代原先复杂难懂的信息须知”似乎成为政务公开与办事指南的基本要求,但似乎有更重要的问题出现了——政府的数字系统如何更为弹性地应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以及人民。
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Recoding America》这本书的副标题吧:Why Government Is Failing in the Digital Age and How We Can Do Better——政府为何在数字时代失败,以及我们如何做得更好?
为什么呢?下面是我所能给出的答案:
“数字政府”是在一个非常严谨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系统所允诺批准并最后投入财政资金人力来实施的现代化工程,而我们对数字政府的期待却是“颠覆现有流程”、“重塑决策体系”、“打造扁平管理结构”等这样一些天真而美好的愿景。虽然“数字政府”表达了开源、众包、扁平、普惠等诸多创新愿景,但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与任务本身却必须被传统的科层制行政系统所承认和允许。数字政府建设的外包服务厂商与决策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诉求不一致,不要被“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而蒙蔽,平台的“涌现效应”也可能违背最初的构建理念。
如果观照现实,“政府数字化是一把手工程”这句话也有两种理解:一是“搞一把就收手”,二是“成为推开下一代政府之门的‘门把手’”。
回头再来看2016年我与其他研究者合著的那本《互联网+政务:从施政工具到治理赋能》,那时“互联网+政务服务”刚刚被提出,移动互联网在中国方兴未艾。我在书中提出,中美数字政府发展的道路选择与差异核心在于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差异以及平台企业参与数字政务的模式差异。而现在从詹妮弗·帕尔卡的《重新编码美国》来看,中美数字政府发展还需要更多审视,比如美国数字政府的荣辱基本来自几十年前颁布的法案,而中国则更为灵活地用规范性文件来调节每个阶段的数字政府发展重点。中国的平台企业凭借无所不能的在线服务触达能力为数字政府点燃了火箭助推器,而以Code for America为代表的公民技术社区公益组织,为美国政府与公众需求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渠道和纽带。
2021年,乔·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转变联邦客户体验和服务交付以重建对政府的信任”,该命令指出,当政府证明“其程序除了公平、保护隐私利益和透明之外,还有效且高效”时,就可以重新获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看似作者在《重新编码美国》一书中提出的问题都将得到了解决,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在一个数字化造就的“无处不在”的政务服务环境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却跌到了谷底?
“Recoding America”,我将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为:需要从文化、基因、意愿等层面,对法律、制度、规范等支配政府运行的整个意义系统进行“重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