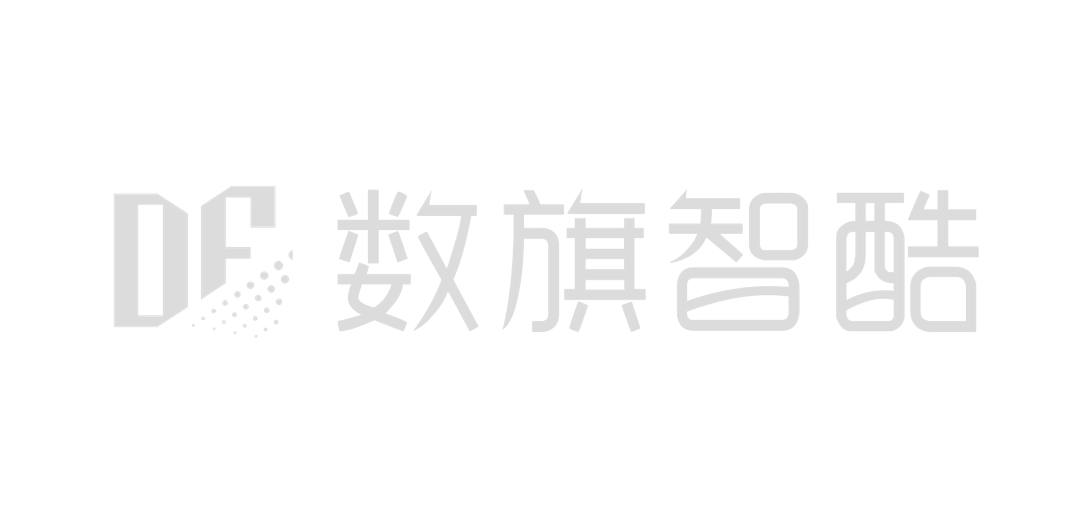作者丨冯 奎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唐 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与表达权利的释放,城市民主逐渐以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贯穿到整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而城市民主质量也与不同城市的平台治理、舆论管控、话语调节、法律意识以及市民社会成熟度息息相关,并影响最终的结果。2006年12月,美国《TIME》杂志将年度人物定为“YOU”(你),即全球网民,每一个改变信息时代的消费者与创意者,并将驱动这种改变与发展的动力源泉称为”Citizens of the New Digital Democracy”,即“新数字民主主义”。这是史上首次将公民、民主以及数字化联系在一起,并首次承认来自虚拟空间的“网络公民”成为改变世界与城市的重要力量。之所以选择“YOU”作为年度人物,《TIME》认为,2006年的互联网已发生了从公众机构向个人用户的重要转变,为此,他们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叫做“新数字民主主义”的概念。“新数字民主主义”与以前的“数字民主主义”的区别在于,传统的“数字民主主义”强调以网络为载体,以高速广泛传播信息作为特点,以满足不同层次和群体的信息需求为目的。“新数字民主主义”象征着一个初具规模并对现实世界运行产生影响的网络社会正式确立,一个与现实社会的平行、互融且自有其生长规律、发展目标的数字社会正在形成。
由于数字时代城市民主的发生前提是基于城市市民的数字表达设备、平台与通道的获得与应用,那么当一座城市不具备网络热点覆盖、智能设备应用以及具有数字素养的市民的时候,这种城市则很可能成为“数字沙漠”,也就不具备实现城市民主的基本条件。“数字沙漠”一词源于一个名为“徐霞客计划”的城市数据共享平台,[1]主要以新浪微博、Flickr这两个社交/共享网站的数据为基准,如果一个面积为1平方公里(仅指城镇建设用地)的地理格子内曾经发出的信息总和少于6个,则把它视为一块“数字沙漠”。根据数据研究显示,七台河市是数字沙漠比例最高的一个城市,上海是中国数字沙漠比例最小的城市。数字沙漠比例最低的前十个城市其中有8个城市要么是省会城市,要么是副省级城市,只有第10低的温州是唯一例外,自然,这座以商业闻名、市区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应该被视为大城市。然而,若是反过来,要说省会、大城市必然数字沙漠比例低却并不正确。乌鲁木齐的数字沙漠比例就高达29%,算得上数字沙漠问题比较严重的城市。全国数字沙漠比例最高的15个城市,东北有8个,西北有4个,前五名全部是东北城市。而数字沙漠比例超过40%的城市,只有一个山东临沂不属于东北和西北。因此,从城市民主的实现难易程度而言,大城市或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要易于地级市或县级市,而东部与南部城市要易于东北和西北城市。
马修·辛德曼在其所著的《数字民主的迷思》一书中指出,以政府网站、BLOG、BBS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一方面充当了市民表达自我主张与诉求的通道,成为民意汇聚和涌现的平台,但另一方面也并非全部真实地体现了民意,同时也包含了部分“带面具”的虚假的民意。而在当下,在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等)、表达形式(图片、视频、直播等)以及表达技术(合成媒体、Deepfake等)的综合作用下,城市民主的本质即包含了真实的市民与抽象的网民面对同一种真实的不同价值取向与解读能力的博弈。20世纪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指出,“民主大众化”是互联网时代下的文明形态转型的趋势之一,民主的形式正在由因成本过高而被逐步抛弃的“直接民主”、少数精英控制的“代议制民主”进入到“互联网技术驱动的直接民主”阶段。互联网革命极大地降低了直接民主的制度成本,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技术可能性,民众直接拥有政治资源与参与政治生活是大势所趋。[2]而城市民主得以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互联网驱动的直接民主形式就是城市民主的重要特征。因此,城市民主依托于数字化技术成为“人人享有的民主”,不仅使每一个市民具备自我发起议程以及推动议程的权利,同时,也让市民具有发现议题、整合议题、放大影响和提升自我辨析度的能力,通过“随手拍”拍摄违章停车就是参与城市交通治理的方式,通过在线定位发布城市积水的图片和信息就是参与城市内涝治理的方式,通过物业电子投票系统参与业委会投票选举就是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方式。
城市民主视野下的“民意”随着网络舆论环境、网络空间秩序以及市民表达能力的发展,也不时会陷入“新数字民主主义”与“网络民粹主义”的拉锯式陷阱——每一位市民自以为拥有了表达的权利和能力,但还不具备参与议程设置和推动议程发展的素养与智慧,从而使“被消费”、“被利用”以及被技术意志裹挟成为不可避免。“药家鑫事件”则可以说是城市民主实践进程中一个有瑕疵的案例。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将张妙撞倒并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引发舆论热议;10月23日,药家鑫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而在案件审理期间,张显作为受害人张妙的代理律师多次在个人微博以公布“疑点”的方式蓄意暗示药家鑫家庭“有背景”,将正常的法律流程解读为“有黑幕”,甚至导致药家鑫辩护律师的正常辩护行为也被网络水军曲解,从而引导网络舆论一边倒地倾向认定药家鑫为“官二代”、“富二代”,推动了网络民粹的“仇富”、“仇官”心理蔓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正常的法律流程与审判意见。2011年4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家人经济损失费;药家鑫随后提起上诉。2011年5月,二审判决宣布维持原判;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2010年正是微博全面开放运营的“元年”,而掌握了新的表达方式与城市民主参与工具的市民并不理解这种工具的“锋利”程度与使用方式,从而使“药家鑫事件”实质上成为了一种面向城市民主进程的“祭品”。
城市民主作为一种城市治理创新的全新理念,并非描绘了一个完美的新世界,而是需要时刻警惕和提防来自数字化平台之上的“乌合之众”和数字化系统内生的“机器民主”的僭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这其实代表着诸多处于城市事件暴风眼中的市民心理,当一个从未获得表达自身价值观与权利的市民偶然获得了在千万网民中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进行“广场演讲”的时候,网络曝光度、知名度带来的眩晕感以及表演心理会加剧“站在蛋的一边”的同情心与“替天行道”的朴素正义,从而失去对真实的判断,将“支持弱者”与“数字公正”划等号,这也是诸多城市民主实践最后屡屡被“证伪”或“反转”的原因。而这背后则是要求权威机构与公共部门需具备自身的信用度与传播能力。而这一点在2020年11月21日突发于上海浦东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位于浦东新区祝桥镇、张江镇涉及的小区确诊病例被公布后,上海市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务新媒体等方式对外发布了最新情况,透明、高效、专业和迅速的城市政务公开,使市民的在线讨论与互动并未引发恐慌以及骚动。11月22日晚上由于要求浦东机场工作人员进行连夜全员核酸检测,“浦东机场”迅速窜上微博热搜,且陆续由可能发生踩踏事件的大量人员滞留视频被网友发布在社交平台。微博及微信朋友圈关于“浦东机场”以及上海疫情的讨论众说纷纭。11月23日上午,“上海发布”官方微信发布了浦东机场连夜核酸检测的相关说明、报道以及现场有序检测的视频,网络舆论迅速降温,市民与网友对上海市政府及公共卫生部门控制疫情的信心也随之上升。这本质是一则城市政府与市民围绕同一事件共同努力促成良好结局的城市民主实践案例。
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对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发现,数字时代的城市民主实现可以看到“广场政治”的影子。“广场政治”缘起于希腊城邦时代。当时每个城邦的中心都有一座广场,广场是市民聚会和议政空间,象征着平等的权利和共和价值观,在西方或中东许多国家,每个广场的历史就代表一座城市或国家的历史。法国《世界报》认为[3],广场政治并不善于建立一个秩序或规则,但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去破坏和打碎一个秩序或规则。但是,数字时代的城市民主形态类似于“新广场政治”,城市政府与市民作为公共事件的平等参与者进入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同一个互联网广场,获得的点赞、转发、评论即代表了各方的支持者和拥趸,当这些数据在平台的参与热度超过了临界点,那么某一方的力量就有主导议程的能力,所谓“意见领袖”以及舆论引导的能力即开始出现。与传统“广场政治”所不同的是,“新广场政治”往往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围绕同一种共同利益进行辩论与博弈。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演进,除了城市组织与市民个体对公共事件的参与之外,在城市民主进程中一种暂时无法定义但又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在受到关注——数字平台与智能机器,通过平台用户大数据的沉淀与算法模型构建,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平台正在成为一种“劝说工具”[4]——从通过商业广告劝说用户购买商品,到通过政治广告劝说市民投票。人工智能已经逐步嵌入到城市民主的规则系统,没有获得政治身份但又有政治参与能力的技术力量化身,在具体的选举投票、政治游说以及公共事件的评价中发生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数字时代城市民主实践比较警惕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虽然平台与机器尚无法以“劝说”的方式“整合”市民手中的选票,但是其在重大公共事件中通过商业意志对平台内容与数据进行“打榜”、“置顶”、“限流”、“屏蔽”等动作,已暴露出了数字平台与智能机器影响城市民主进程的根本能力。比如盘踞在微博平台的明星经纪公司通过购买“热搜”实现偶像打榜的流量运营方式,比如微信平台在公众号信息流运营方面通过对不同内容进行限流以突出其在原创内容选择方面的运营价值取向,这都将影响城市民主治理与质量。
在“7.20郑州特大暴雨”中,朋友圈中一份“救命文档”的出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021年7月20日20:57,一位在上海财经大学就读的大学生Manto在腾讯文档上创建了《待救援人员信息》,敲下第一行字:求救人员信息,救援人员信息。在此后的24小时内,这个文档更新了超过450个版本,浏览量超过250万次,保守估计数千名志愿者对文档做出了编辑,成为众多民间救援组织进行救援信息收集的在线表格。
“救命文档”的“可编辑”特性是数字治理时代“参与感”的高级形式,同时代表了一种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趋势,真正体现市民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价值与行动力。在“救命文档”的实践过程中,“可编辑”正在成为一种融合了参与、校正、核验以及持续向前发展的公共责任表达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档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求助信息”“避险地点”“漏电地区”“官方救援队信息”“民间救援队信息”“物资援助”“心理疏导”“医疗信息”“给河南加油”等20个分表格,甚至衍生出了英文版本,由志愿者完成对核心信息的翻译。在其他文档协同平台上,也存在类似承载大量救援信息的表格。上面的每一个小方块,就像一个接力棒,等待在现实中人们确认、寻找、帮助、救援。
“救命文档”一方面体现了个体力量在城市治理数字赋能下的强大势能,另一方面,其“有限匿名性”也让参与者更多关注救援目标状态,无限接近于信息的真实性,而非关注“谁在说”、“谁的态度更好”。“救命文档”让每个参与者都成为决定了信息质量甚至生命安全的“责任编辑”,而非一个吃瓜心态的评论者,每个参与者都成为一个“纠错者”,而非社交媒体言论极化趋势下随处可见的“抬杠者”。而正因为对生命的尊重抑制了在社交媒体上时常歪楼旁逸斜出的“吃瓜心态”。在“救命文档”的表格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节点”,他们在传统的应急指挥团队、官方救援热线、受灾群众安置点这些“节点”之外形成了有力的补充,极大地缩短实施救援和自救的链接路径,从而成为彼此的救助者。
相比于传统城市政府治理理念而言,数字技术、平台与算法营造和构建的城市民主环境,一改往日的统治与被统治、命令与服从的陈旧范式,在去中心化的组织设计、开放议程设置、“没有中心思想”的行动路径以及流动式开放参与等特征之下,通过平等对话、交互与博弈,最终实现了双方在治理智慧与公共精神上的共同成长。而在城市民主参与公共治理的创新理念引导下,加强对网络传播特殊环境下的真实民意“辨析”,提升对互联网商业平台的监管能力,排斥和剔除基于数据、算法和算力共同培育的“智能机器”对城市民主的干扰与侵袭,这是数字时代城市治理必须面对的未来。
本文节选自《数字治理:中国城市视角》

[1] 赵新宇,大陆城市“数字沙漠”调查,《香港凤凰周刊》,2015年第18期
[2] 朱嘉明,互联网文明和中国制度转型,《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东方出版社,2019年2月
[3] 广场政治,为何在中东能量惊人,《环球时报》,2013年7月17日
[4] BBC纪录片,《智能陷阱:监视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