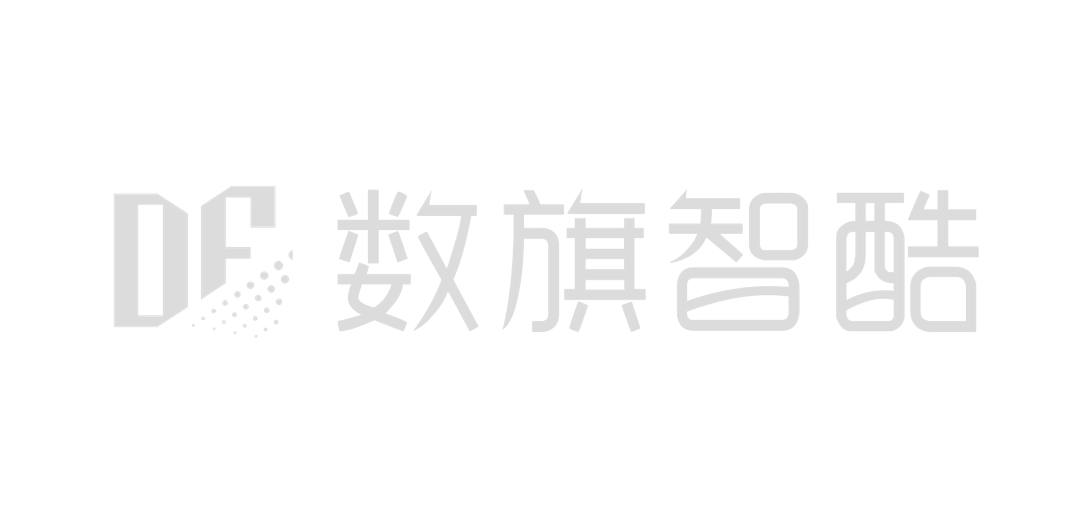作者丨冯 奎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唐 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其一项研究中指出,中国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仅13个,而中国80%的城镇居民居住在50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该研究预测,中国将出现100多个人口数量介于50万和150万之间的新兴城市,并在2025年将形成“分散式”的发展模式,同时还会新增60多个总人口数为150万至500万的中等城市。从现有趋势来看,中小城市将会成为经济增长引擎。麦肯锡预计,至2025年将会有70%的人口居住在总人口数不足500万的城市,这些城镇带来的产值将占到城市GDP的一半多。城市型社会正在来临。
城市型社会,是指中国已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北京、上海、天津已迈入高级城市型社会之列,广东、辽宁已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另有10个省份刚刚跻身初级城市型社会之列。从国际经验看,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主要有城镇人口、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关系五个标准。其中,城镇人口标准是最为重要的核心标准。以人口城镇化率来对城市型社会进行阶段划分:城镇化率在51%至60%之间,为初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61%至75%之间,为中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至90%之间,为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为完全城市型社会。从城镇人口和空间形态标准看,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但是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看,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具有一定差距。例如,从生活方式标准看,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县改区中存在的大量农民,虽然已被统计为城镇居民,但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从社会文化标准看,中国的城市还是建制镇,大都缺乏特色,城市文化缺失,城市品质较低。从城市协调标准看,中国的城乡差距仍然过大,促进城乡融合共享和一体化仍任重道远。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至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60.60%。因此,我国正在由初级城市型社会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
城镇化的数量增长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城镇化发展的核心特征。追求数量增长、以数量增长为荣,是普遍的执政心态。所谓数量增长,主要表现就是城镇统计人口增长较快、高楼大厦建设较快、支撑这种城镇发展的传统产业增长较快、城镇面积往外扩张较快。[1]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数量从 1978 年的 193 个到 2000 年增加到658 个,再到 2019年的 672 个。并且,中国近2万个建制镇中人口超过 10 万的镇已达300多个,这些镇均具有“城市特征”,2019年温州市龙港镇“撤镇设市”也代表着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2019年摩根士丹利发布蓝皮书报告《中国城市化2.0: 超级都市圈》认为,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5大超级都市圈的平均规模将达到1.2亿人、城际通勤铁路里程较目前增长8.5倍、万物互联和数据市场将达到1万亿美元。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升至75%,即增加2.2亿新市民,这主要得益于三大支柱:一是城市群兴起將发挥集聚优势,同时缓解大城市病;二是受益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智慧城市将减少交通拥堵、安全隐患和污染;三是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有助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农村人口迁入城市。[2]
从中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价值定位来看,基本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3]:
- 城市化1.0阶段,即把现代城市理解为一个形式系统,该阶段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现代城市形态和内容要素的简单模仿与照搬,中国城市发展处于典型的追赶阶段;
- 城市化2.0阶段,即把现代城市理解为一个经济系统,该阶段主要表现为风行全国的经济开发区模式,中国城市发展在本阶段主要与经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处于一个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博弈、城市发展以透支农村劳动力为代价的“野蛮生长”的突围阶段;
- 城市化3.0阶段,即对城市的土地与空间价值产生觉醒,城市土地交易系统作为政府发展经济的金融工具,城市空间作为政府进行城市营销的巨幅立体广告。该阶段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新城模式和开发商主导的房地产模式。中国城市发展在该阶段一方面在“大拆大建”中探索城市的发展禀赋,另一方面“新市民”由城市建设者与“主人翁”的转变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城市民主的实现;
- 城市化4.0阶段,即由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基建,城市被定义为一个“硅碳合基的超级智慧系统”,在强调于物质空间中营造城市硬件系统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城市软件系统的建设。该阶段主要表现为政府对“智慧城市”和“新基建”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进。本阶段的中国城市发展陆续经历了从“技术之上”、“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探索过程,其中,“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一网统管”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城市发展新浪潮不断涌现;
正在到来的城市化5.0阶段,是由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共同构成的“机器崛起”的城市化时代,目前在迪拜、日本的机器人已经在机场、警务、交通等领域应有,中国城市的智能化发展在这方面并不落后,这也是中国现代城市文明从对西方的艰苦追赶转向成熟的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本阶段的中国城市完成了基础性的硬软件建设之后,城市发展的价值重心势必要转移到“人才是城市的目标”上来。城市不仅需要具备能量与智慧,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容纳“人”的情感、承载社会的意义。
因此,可以看到近年来在各类新闻媒体与社会学调查在关注全国各大城市市民的“孤独感”、“性生活质量”、“老年人情感陪护”、“婚姻幸福感”话题等日渐增多。东莞的中年农民工在失去工作准备离开城市返乡之际,通过在东莞市图书馆留言簿表达自己对一座城市的感激,留言最后登上社交媒体热点,最终被城市公共部门挽留。寄居于深圳市龙华区人才市场因为债务或贷款无法回家而通过零工日结的方式流浪在城市的“三和青年”也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灰色群体”。他们都是中国高速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缩影。

中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价值定位
从当前我国城市数量、体量、质量以及整体城市化率来看,我国城镇化发展仍将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并将因管理、经济、技术和社会等方面影响呈现出一些新特征。[4]首先是城镇间人口流动比重不断提高。通过手机信令的监测数据结果显示,2017年在新增跨市域流动人口中,以县城和市区作为流出地的比重为36.1%,2018年上升为39.2%,2019年则达到45.1%,呈快速上升趋势,未来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城镇间流动人口问题。而这背后的人口流动加速,除了传统视野下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外,基于数字平台与数据共享推动的城市数字服务供给也成为一大亮点,如在公积金、社保、就医等领域的在线查询、缴纳以及应用。其次是大城市承载人口比重上升,城市出现分化,且这种分别不仅存在于基于城市等级化管理体制下的资源分配、户籍门槛以及公共服务能力,更在于不同的城市群体在面对城市服务与问题上的反应与参与能力,比如缺乏公共精神与数字素养的农民工群体、尚未具备自我操作智能化设备能力的老龄化群体以及虽然生存困难但因为程序复杂而不愿主动申请帮扶支助的困难群体,这些群体很可能是在城市人口比重上升背景下的“沉默的大多数”。第三是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老城改造与传统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备受关注。在涉及城市无线网络、物联网传感器、智能摄像头等均成为未来城市提升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以适应城市型社会发展的重要建设内容。
虽然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生产结构发生转变以及基于数字化发展的“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不断突破城乡界限[5],对于城市型社会的发展不仅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随着区域间城市化发展逐步走向平衡,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格局形成[6],以及以数字科技、节能环保、康养服务为主题的新兴城市不断涌现和崛起,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进入新千年后,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浪潮的席卷,中国城市化发展逐渐具备了对标世界城市发展的资格与能力。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2020全球城市指数报告》显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和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仍领衔前四。在中国城市中,北京超越香港,历史性地进入全球第五名。在2020年《全球城市综合排名》中,中国内地城市表现持续提升。除了北京之外,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南京、杭州、青岛、成都、重庆、武汉等“新一线”城市也有显著的排名提升。上海跃升至全球第12名,排名上升7名;深圳上升4名;广州上升8名。杭州继2019年首次进入百强后,2020年上升了9名,位居82名。成都排名提升2位,位列87位。西安上升9位,首次进入百强城市。南京维持第86名。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春季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武汉,此次排名仍然提升了11位,从去年的104位进入百强以内,居93位。武汉市的排名提升幅度,也超过了绝大多数内地城市。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老牌一线城市已进入与世界城市角逐的竞争序列,以成都、武汉等位处中西部的城市也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支异军突起的新兴力量。2018年,GaWC《世界城市名册2018》报告主要编写者、GaWC副主任本·德拉德与凯瑟·佩恩表示,世界城市发展已逐步向亚太地区倾斜,同时,随着更多中国城市加入其中,世界城市或将迈入“中国世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显示,中国有9个城市进入全球前50名,39个城市跻身全球200强。报告的评估数据表明,城市在世界网络中的不可替代性越强,排名就越高。报告主要作者、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2019年,在前200名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城市中,亚洲城市数量增加,欧洲城市数量下降,这反映出“全球综合中心和科技中心(的重要性)总体提升,专业性城市和制造中心总体下降”。因此,从上海打造“全球科创中心”、杭州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贵阳打造“大数据之都”等可以看出,面向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与发力,将城市打造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产业网络节点与吸聚人才的光源,而不单纯依靠土地、劳动力、政策等传统资源,成为数字时代城市竞争的新轨道。
城市在科技与数字化方面的投资吸引力与竞争力以及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价值作用成正比,这一点在持续得到印证。根据2020年毕马威发布的《城市技术的崛起》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以共享居住和众创空间、移动出行、配送、智能城市、建筑技术和房地产技术等为代表的城市技术正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技术的崛起反映了城市和城市化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平台,取代企业成为当代经济的基本组织单元。

2016-2018年领先城市技术类型

2016-2018年领先城市技术国际城市
亨利·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与政治》中指出,进入都市的权利,不是一项自然的权利,也不是一项契约性的权利,它指的是城市居民的权利,还有那些在交通、信息和交易的网络和流通中出现而结成(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团体的权利。[7]而在数字时代的城市型社会之上,进入都市的权利对于市民而言成为一种“双重契约”,一方面需要与涉及交通、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形成契约,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城市服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出行服务平台等形成契约。前一种契约来自于城市人的社会身份,后一种契约则来自于数字身份。未来,这两种身份的融合、互动与博弈构成城市型社会未来发展的核心基调。
此外,在平台、数据与算法的支撑和驱动下,城市型社会的发展不仅对城市政府机构、公共部门、企业组织的运行以及需要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刷新,同时,也在重新定义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的“亲密”与“疏离”,将现代都市社会由一个“陌生人社会”由智能推荐、人脸识别以及大数据算法建构成为一个介于“陌生”与“熟悉”之间的数字化社会,“陌生”是指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长与流动导致人与人的实际关系仍然保持陌生,而“熟悉”则是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场域的智能机器、设备与镜头都在时刻准备验证每一个城市人的身份,以确认“你是你”。相比于伦敦、纽约、利物浦等老牌城市在工业革命时期就步入城市型社会阶段,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断裂变与城镇化、工业化、老龄化叠加演进的中国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型社会的形成与演进尚有诸多亟待被发掘与研究的空间。由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城市在诸多领域正在扮演着面向数字时代的新潮流、新问题、新趋势的引领者、发现者与探索者。
本文节选自《数字治理:中国城市视角》

[1] 冯奎,城镇化发展将出现新特征,《中国发展观察》。2014
[2] 《中国城市化2.0: 超级都市圈》
[3] 未来的人文主义城市精神 常德老西门城市生态,https://kuaibao.qq.com/s/20200921A02PAG00?refer=spider_map&openid=o04IBALjBJA9U7h-QovH8qrr48-I&sec_share=sec_share,《城纪》,2020年9月20日
[4] 范毅,城镇化发展的新特征,《北京日报》,2020年7月27日
[5] 电子商务、社交电商带来的消费下沉、品牌下乡,以及扶贫纾困带来的农产品进城。
[6] 徐林,范毅,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城市化,《比较》
[7] 亨利·列斐伏尔著,李春 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