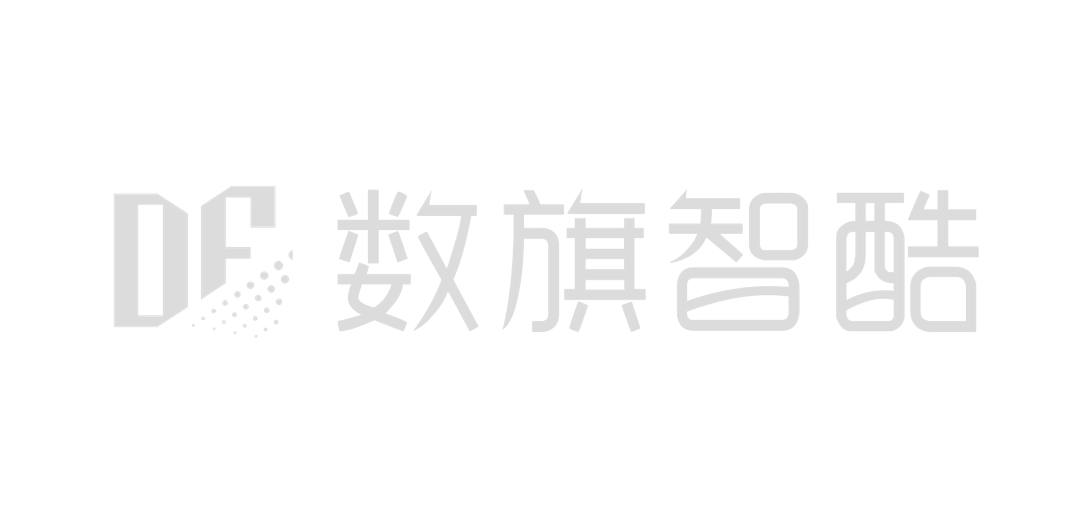2022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DI)得分从2020年的0.7948提高到2022年的0.8119,全球排名第43位,是该报告自发布以来排名最高的一次。比起2020年的第45位,提高了2名。在三个主要指标的得分上,我国在“在线服务”指数上的得分相对最高,为0.8876,在“电信基础设施”指数上的得分为0.8050,在“人力资本”指数上的得分为0.7429。
从报告的数据和结论可以看出,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对数字政府未来的关切与思考。
○○○
地球不是平的,那些凸起和凹陷的部分就是数字化形成的海拔和沟堑。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亚欧大陆与大洋洲以及小岛国,资源、产业以及治理能力在拔高和降低不同城市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海拔,人口越多的城市在数字化预算、技术人口聚集等方面更有优势,也由此导致其在线服务水平更高。这可能就是数字政府的“虹吸效应”。从这一点来看,上海的在线服务指数位列全球第十,似乎更符合一种“城市人口决定论”。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否说明,政务服务平台的价值逻辑开始越来越趋近于平台经济(梅特卡夫定律)的本质——用户数量越多,网络价值越大。
所不同的是,平台经济竞争的不是市场份额,而是市场本身。而政务服务平台的根本价值在服务事项本身,或者说权力本身。平台经济天然具有价值扩散与垄断性质,其服务能力来自于对市场的触达能力和渗透能力,而政务服务平台均具有极强的地域属性,尽管跨省通办在打破“数字割据状态”,但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能力本身并非全部来自其服务设计和体验本身,且主要来自用户的制度性诉求——所谓“不得不用”的那部分服务。
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发生时,为了避免出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陷阱”——生产效率提升、工厂利润提升、工人工资停滞不前、“卢德分子”出现,于是“20世纪的新社会契约”开始浮现——教育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与升级,让工人避免进入新的“技术陷阱”,从而催生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兼具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名词,不仅代表了一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性成果,同时,其所掌握的政策参与能力也让技术发展进入一个大平衡阶段。
2020年疫情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年度演讲时,呼吁通过“新社会契约”和“全球新政”来消除社会不平等。他表示,新冠疫情大流行暴露了数十年来被忽视的风险,包括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社会保障欠缺、结构性不平等、环境恶化和气候危机。同时,他强调各国政府需要优先投资数字扫盲和基础设施,使社会为包容性、可持续的数字未来做好准备。
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当下是否已经具备面对数字鸿沟达成“新社会契约”的条件?从过去几年的实践来看,由科技企业、互联网平台以及政务服务平台来推行的“尊老模式”、“无障碍模式”等并未实质性地减缓和降低老年群体、少数群体面对数字社会“硬着陆”的速度和摩擦力。下一步,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这样一些眼花缭乱的技术、模式或愿景能否给予我们更好的数字未来?我并不乐观。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数字空间不是让现实中的被抛弃者获得新的领地与机会,而往往会复制与加剧现实中的不平等。
因此,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我们正在经历的数字时代或许与上一次工业革命的境况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需要聚焦数字素养的全新教育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来保障每一个公民避免进入数字鸿沟。可能我们更应该理解的是,与其将已经坠入数字鸿沟的群体“血肉模糊”地死拉硬拽地拖上岸,何不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让他们自由平静地走下去?比如为他们提供符合自我意愿的服务方式。数字鸿沟是一个动态的、每一个人都必将面对的“灰犀牛”。数字原住民与数字难民面对的问题,元宇宙原住民与元宇宙难民同样会遇到。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AI时代,每一次数字浪潮的转轨都有一批人进入数字鸿沟。在移动App上如鱼得水的我们,在元宇宙中也可能近乎一个“乡下人”。
无论如何,我觉得数字政府正在开启新的篇章,不只是中国,也包括世界。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就像2016年之前移动互联网以及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不可忽略一样,对于“中国数字政府的未来”,不可忽略的可能是“党的领导”与国企央企主导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安全先于创新,谨慎多于冒进。这可能成为数字政府领域新的主旋律。
报告指出,在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等部门,重点更多的是学科专业知识,而不是数字技术的熟练使用。如果以2020年的疫情为界,之前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多侧重在于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政府部门,从此以后将更多关注专业知识如何赋能数字应用。数字机器更擅长的是帮助人做决策和选择,而对于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而言,所有的公平、正义和平等往往来自于决策之前的比较、分析以及有温度的思考。所以,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所谓“提升数字素养”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工作人员如何更好地掌握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人的数字素养;二是工作人员如何将自身积累的专业知识与产品经理、程序员、研究人员等一同“喂养”给数字机器,提升机器的人文素养。
《算法的力量》一书指出,数字技术即是政治本身。的确,只是数字技术所裹挟的“政治”不是来自创造它的人,而是来自使用和决定如何使用它的人。数字技术所包含的对阶级、身份以及权利的态度,虽然是由一群未经选举、任命或任何政府部门入职该有的流程的程序员来设计和开发,但决定使用的是他们背后的整个权力体系。所以当报告指出,“不平等的新面貌”正在以数字化的方式体现,而电子政务可以成为社会的平衡器。我们应该首先感到的是失望与庆幸并存,因为,在科技巨头为了数字空间的竞争杀红了眼,暗网为了利益可以草菅人命的时候,电子政务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这是否也应和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的“数字政府助推数字经济、引领数字社会、营造数字生态”的期许?
报告指出,数字政府的发展不是将现有官僚机构的数字化。数字社会发展的优秀案例表明,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和城市积极寻求消除政府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摩擦点。简而言之,发展数字政府不是为了用数字化来武装一个传统的官僚体系,而是突破传统的服务、治理和协同的瓶颈,构建一种全新的决策与行政模式,这也是将数字化视为一种工具还是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的主要区别。但是,《足够智慧的城市》的作者本·格林告诉我们:任何数字技术的运用都不会是颠覆或革命现有的机制、流程和模式,而是满足、弥补和延伸现有管理体系的需求,正是与现有的考核和激励制度相兼容才会采用它。
此外,数字技术并不全然都是消除摩擦的。当公共部门在治理思想与视角上的局限性被数字技术放大,新技术的生物性、变异特质以及不可控性,将会在政府和公众之间不断制造新的摩擦点。比如用户体验导致的服务质量低劣,比如技术过度滥用导致的隐私泄露,以及缺乏管理优化的重复性“技术赋能”导致的基层苦不堪言。这一点在疫情期间的流调、扫码、核酸筛查、疫苗接种等各个环节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想,如何遏制住数字技术不断放大和扩散社会摩擦才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